刘克襄《十五颗小行星:探险、漂泊与自然的相遇》

《十五颗小行星:探险、漂泊与自然的相遇》适合在夜深人静时分,躺在床上,或俯首几案,跟着刘克襄的文字走进去,走进去那十五个对大自然执着的、痴狂的、“传奇的、漂泊的,或者探险的人物”,生命的故事。
在自序中,有一点是触动着我的。刘克襄怀念起早年带着孩子奔跑野外、攀爬山林的快乐。这是我脑海里勾勒过的图景:如果我有一个小孩,也要带着他/她往山林跑、到野外探索自然。然而,事情很多时候跟我们所希望的不会往同一个方向去,刘克襄的小孩成长后,跟他凝望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乎的是打耳洞、染头发,崇拜的是太宰治。刘克襄说,孩子是星球,或许仍然环绕着父母,但也有了自己的轨道。那十五个故事人物也是,是色泽、明度、成分和质量都不同的小行星。
纤细的文笔,<隐逝于福尔摩沙山林>带给我真挚的感动。一个人,走进阿里山的勇气和精神是动人的。江惠的歌,成为一个寻找失踪在山林的孩子,鲁本的父亲继续下去的力量,也是动人的。一首歌,伴他度过生命中最悲恸的时光。卖膏药的王禄仔仙喊出内容,请大家帮找这个纽西兰金发青年。找到的话,会给奖金,还把珍贵药材送给对方。江湖客的宣传不只是感动了刘克襄,也透过刘的文字感动了读者。一年后,鲁本的父亲得到纽西兰的资助,来协助丰山地震受害者。受访时他说,很欣慰自己孩子的最后,是在台湾山区结束。离开前,也透过电台希望向Judy致谢,有关首歌陪伴他的歌。人间有情,鲁本的父亲在事发后,没有责怪孩子,怨恨台湾的山区,这是对自然的信仰,这是宽阔的胸怀。
<成为珠峰的一部分>写一个叫拾方方的青年,在“老大”的领队下,一同登珠峰,却因为不听领队“老大”的指令,在恶劣的气候下坚持攻顶,意外死在珠峰。这件事之后,刘克襄隐约觉得,“老大那时也没有回来”,曾经怀抱梦想的老大,满嘴酒气,郁郁寡欢,一直觉得是自己的错吧。其实,热血青年拾方方在前往珠峰前已经留书:“……我更不能去掌握我是否能在这次远征活动中活着回来……就算大败,我也不后悔”。“拾方方用他的死,浪台湾后来前往珠峰的三友,萌生宝贵的教训”“拾方方不是不信邪,而是他决心以自己的肉体,印证登山屡见的死亡模式。”那么,经过这些年,老大“他也应该从珠峰回来,该戒酒了”。当我们年轻,当我们执意做一件事时,也应该珍惜生命,顾及会给旁人带来的麻烦吧,这是读此文的感受,但是年轻的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曾这样的执着与一意孤行呢?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只是,梦想实现了吗?
<托泰布典的愿望>,写刘克襄参拜了托泰布典的遗容,三五天便走进托泰布典晚年生活的田园,感觉他的存在,他的族群意识,忖度他遇见日本的鹿野忠雄的青春荣光。鹿野忠雄写自然科学报告,山行札记,最后在婆罗洲的黑暗雨林失踪。托泰布典是他的原住民伙伴。托泰布典跟刘克襄的机缘,是因为托泰布典写信给刘,感谢他这个副刊编辑,愿意大篇幅介绍台湾的探险任务。也因为这样,刘跟托泰布典书信往来,通过他的回忆,对探险前辈鹿野忠雄的一些过往更了解。鹿野忠雄很可能是在15岁时,看了昆虫学者江崎悌从台湾捕捉回去的长臂金龟昆虫,兴起来台湾的决心。“有一种浪漫的迷思,好像任何小孩只要看到它,一辈子就会爱上自然科学了。”通信五年,他一直希望刘能探访他,一起坐在庭院,走在田园小径,闲聊过往。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说他梦见鹿野,应该很快就会见面。果然,一直不知怎么回信的刘,后来就得知他去世的噩耗。刘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他和托泰布典有机会坐在那里,望着山,“我们的山”……这样的结尾,让人动容。
<首登玉山的日本女生>这篇文章比较不深刻。大概是刘写一个不是自己真正认识的陌生登山女子的缘故吧。他猜测,因为日本女子的探险家父亲跳海自杀,整个家族羞愧,便在台湾消失了。
<云豹还在吗>写因为刘的启发,“你”,梦想着能在森林里,看见一只云豹,并执着、认真,选择博士论文的研究范围,以大武山区和双鬼湖地区为主,调查云豹,结果一只没有成绩,导师,一个美国野生动物学者跟“你”入山,病故死亡,再来是你的队员,被洪流冲走。野外调查出的事故引来记着的批评。刘把“你”的故事说给小猎人听,鲁凯族的他,在被问及台湾还要云豹吗?说去做梦看看。后来,他对众人讲解部落故事,就说,他在梦里,梦见云豹在石头趴坐。结尾,刘在你的眼眸见,看到了最后一只云豹,继续初见的场景。喜欢那结尾。
不知道为什么,读<最后的撒哈拉>这一篇,让我感觉有点像为了凑数而写的。也可能是作家本身跟三毛并不熟悉,只通过一次电话,约好要去关度沼泽区的芦苇林,后来就离开人世了的关系吧,写起来比较牵动不到人心。
喜欢<夜鹰的大地>这篇,很有意象。<向老鹰学习>一开始,从一个裸体做飞行姿势为开端,吸引了读者,其实指的是自己让学生看的照片。文章讲述一个自然僧,捐出所有家产,投身“老鹰大业”。最后更选择赤裸,在大自然里,仿佛前生是一只鹰。“那犀利眼神所散发出来的目光,紧紧地勾住了我。那不是在跟我打招呼,而是把我整个人的灵魂,以大头针穿过甲虫般,牢牢地钉死在纸板上”,“鹰——羽翼仿佛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灵性,在我们前面朴实地滑行而过”,这引发了读者的想象,是美妙的。
<戈壁来的呼唤>彭加木,从对他的敬仰,写信想加入他的队伍,没想到他意外失踪在戈壁。慢慢回溯自己的经验,连贯自己遭遇土石流的心境,又联想起彭,反复交错,有一种迂回的情感。“单脚伫立,头埋入背羽。偶有浪花的碎沫,滚过脚前。”
<台风的子民>用平静的语气,带出了两代人对自然灾害的关怀。主题讲的是“你”,——胡德夫(排湾族音乐家,总进入灾区救灾)以及“我们的朋友”,——英年早逝的王志明(以身为汉人为耻辱,带领刘克襄走向人类学和人道关怀)。他们都为弱势族群奔波,王志明还翻译了法国人类学者李维史陀的经典著作《忧郁的热带》,翻译完,就辞世了。在主体中,刘克襄穿插带出了两个女孩在文艺营讲的,有关与家人亲历台风的故事,前一则祖母、父女与山猪之情、后一则父母之爱,夫妻之情。别人的故事写得如此动人,刘克襄的文字功力非一般。最后,他说,“我们以为他们是草莓族,只懂得网路世界,虚拟的时空,失去对土地的信仰。其实,在一年比一年强大的自然灾害中,他们不断遭受撞击,或许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强,更懂得,审慎面对重生。也更懂得,这座岛的宿命。”“反观我们这一代……啊,造成土地受伤的人,其实没什么资格训示下一代……”引人思索。文中有关大自然神奇的灵性,是撞击到心灵的。“森林太安静了,让他心里有些不祥的感觉。”果然,土石流发生了。山猪沙布不顾风雨,跑出来撞门,引女孩一家逃离土石流……“Vuvu(祖母)高兴地跟我说,沙布愿意回来,还带了孩子出现,表示这儿一定是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放心了。”本来,刘克襄有点不敢置信,后来,在灾害播报时,看到一则小林村的故事,说一只狗,靠着天生的本能,在土石流来时抢救了44条人命,他就相信之前少女有关山猪的描述了。身为读者,也为文中的浪漫情怀牵动,“我们做了一艘纸船,把那片小骸放在上头……我是流着泪慢慢送小船出去的……希望它一直飘……飘到他攻读人类学的北美西岸。”“你们是否也把小骨骸带回老家,埋葬在大武山?”
<伸港来的阿嬤>很有趣,文中阿嬤是刘克襄在高铁上遇到的陌生人。起初,他的探问让阿嬤有些提防有些小心翼翼,后来却“一不小心聊熟了”。因为阿嬤来自的地方,是他最早赏鸟的地点,所以他“隐然感觉,自己和阿嬤有一种熟稔的在地关系”。透过与阿嬤聊天,他回忆自己在那里赏鸟的经历,以及了解别后那里的生态环境(阿嬤的弟弟,被聘在伸港当虾猴看守)。阿嬤固定带海产,到台中第五市场卖。短短不到半小时的车程,他写的全文通顺好读,很温馨,这又见功力了。
<老农溪上游的小村>写部落,布农族人,保育塔罗流吸。竹桥,不喂鱼,保持大自然的风貌,保育生态不纯粹为了观光,而是共生。最后遇上台风,一切归零,但是刘相信,他们会继续坚持。“因为简单惯了,因为一无所有,他们会继续坚持吧,我真的如此深信着”。
<冬天的怪婆婆>这写不是所有居住在偏远茅屋、森林里的农家,都是亲切、淳朴的人,有些离群寡居、愤世嫉俗,就是不喜欢陌生人接近。刘克襄大概本身是个亲切的人,忘记了世间本来都是多元的。一行人,得到怪婆婆不友善的对待,先因为觉得房子漂亮,建筑结构很美,照了相片被骂“偷拍”,后来又因为在野外挖采嫩笋被叫做“贼仔”,刘克襄为了以后还能坦荡荡做人,坚持向怪婆婆解释,虽然她最后还是赶他们离开,至少他的内心是踏实的。
<新中横的绿色家屋>写柳暗花明,下榻幽深处的民宿,“老五民宿”的经历。那和风味的民宿,远离农药的环境,女主人制作的全买手工馒头,原生树种等,都让人向往。也唤起许多属于自己的经历和遇见的喜欢的民宿。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了吧,引起共鸣。“农药真能治虫吗?害虫依然生生不息。反而是农药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依照大自然的法则,农作物只能收成一半,但人全都要……生活当然腹语了,精神却变弱了。”在哪风灾、土石流等,精彩样机的有兰溪畔,他们在最不安稳最恶劣的环境,营造有机家园。大家一起不用药,整体环境才可能改善。
<家山>是上山,林家三兄弟,一个老太太(清裕婆说),梯田、茅草屋,和刘克襄之间的关系。有关雪山隧道开凿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老人的坚守。对于,是否跟后一代谈,老人的态度是(清裕婆说):免烦恼啦,后一代伊们要做什么,伊们自己决定,咱们做给自己,欢喜就好……“种一期稻子的收获量,便足以不虞生活……梯田有了重新滋长休息的机会。”抽水马桶成了突兀的设备。茅坑入册。
十五颗小行星:探险、漂泊与自然的相遇. 刘克襄著-初版-台北市:远流,2010.06
阅读日期:2016-06-13--2016-07-07
书源:Jurong West Public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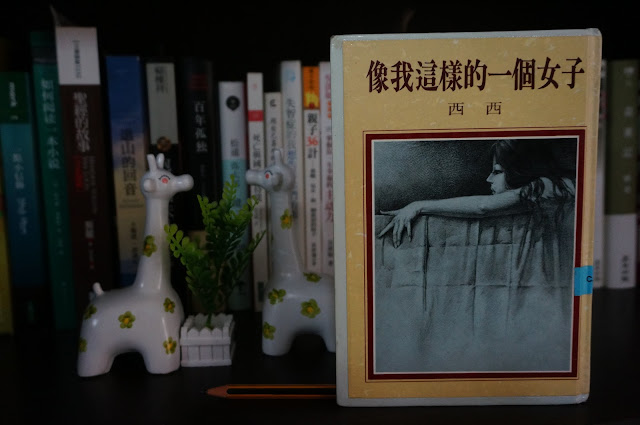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