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陀螺

我又聽見男人的喘氣聲。冗長的、沉重的,劃破在四面八方的空氣裡。我把耳朵貼近牆頭,長方室裡的四面牆。我把耳朵靠在地板,冰冷的花崗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聲音,自哪一個方向傳來。
男人的喘氣聲,纏住了我的耳朵,貫穿入我的喉嚨。我禁不住喊噭。
屋友公幹還沒回來,屋友沒回來。這房子就我們兩個住客呀!哪來的聲音?
“你再不搬出這所房子,就別想把他的影子驅逐!”我不記得這是第幾次,阿行這麼告訴我。我的胸口被幽靈盤踞著,喘不過氣。
房子是阿黃給我租下的,他讓我搬進這所房子時我說我怕,這裡離大學偏遠,環境雖然清幽,獨立式的小洋樓雖然舒適,可是鄰家遠遠的東一間、西一所,唯一的屋友常常到外坡公幹,我一個人多恐怖呀!阿黃說沒事,屋友不在時他一定過來陪我。
後來,他在床上吻了我;懷抱著撫摸著我的腰身。他在廳裡繪畫,落坐於沙發上的我的腳踝。他在澡間把香精泡泡,吹上我的髮絲我的肌膚。有他伴著呀,我無畏。
阿黃,是我的講師。驚訝吧?他有古銅的膚色,高大的體格,掛著魚尾紋的眼角。大一那年,我上他的第一堂課:攝影班——
“學攝影,最基本的,我們得掌握快門的知識與運用技巧……”他的聲音低沉,平平的沒有調子。同學們都不專心,我卻架著臉龐張著耳朵,生怕錯過一字一句關於攝影的基礎知識。
第一次呈堂,阿黃把我的作品張貼在辦公室外的佈告欄。那是我第一次用專業相機:省吃省用,以獎學金餘額籌以我的兼職薪金買下的,千二塊的Sigma SLR相機。我的攝作裡,老爺爺握著老奶奶的手,漫步在公園的小徑上。小徑兩旁的大樹下,是落了一地的黃花。黃花淡淡的色彩,彷彿散發著芬芳。芬芳,與老爺爺老奶奶的愛調配著,調配成溫馨與幸福的味道——迂迴。我在公園裡把感覺捕捉的那刻,幻想著他們是我的父親,我的母親。父親牽著母親的手,漫步在公園裡。
“你照得很好啊!”我在阿黃辦公室外看見自己的作品時,阿黃剛好走了出來。那是阿黃第一次讚我,那時候,我稱呼他黃老師。 “你這孩子很有天分!”我閃爍著眼神,望了黃老師。他濃濃的眉、高高的鼻,豐厚的唇:這麼好看的男人,除了我爸,我再也沒有看過第二個!
“黃老師,我……”
我隨即想起了父親,想起了自己,想起從小就喜歡攝影油畫與書法。只是,母親從來沒有閒錢供我學畫練字搞攝影。母親 說,這是有錢人奢侈的玩意兒!母親也說,藝術家的命運是餓死街頭。母親含辛茹苦地把我養大,我不便違母親心意執意念純美術,於是報考大學時申請了建築系。原以為美術從此套上邏輯,呼吸在剛骨水泥間,不料還能修念美術學院公開的攝影學科。想到這裡,我哽噎。
有些男人,看見女人的眼裡翻滾著淚水,便會衍生一萬個心疼。黃老師把我帶進他的辦公室,讓我坐下,給我倒了一杯開水:“喝吧,方小玉。”我的眼睛,終於灑下淚花。“深呼吸,深呼吸……”黃老師溫柔的目光淋浴著我,像要把我的苦楚都挑去。他低下頭翻開抽屜,取出一張紙。
“啊!怎麼會……”那是第一堂課時,我在作業簿裡撕下的一張紙。紙上鋼筆草繪了兩個男人的輪廓:一個是父親,一個是黃老師。紅霞,散放在我潮濕的臉頰。
“這個,是誰呀?”黃老師故作沒事,指著畫中我的父親,問。他的眼神,流露出靈魂裡的虹。
“遺——棄——我——的——爸——”我卻感傷家世,悶氣沉沉地壓上胸口。
那天,我們談了整個下午。我翹了一堂課,黃老師不知道。
那天,我們談了整個下午。我翹了一堂課,黃老師不知道。
黃老師說,他教油畫呢!只是,油畫班不開放給非美術系的學生。他告訴我時,我不無失望地長嘆。“但,我能教你……”
“哦?”
黃老師把我載到校園範圍以外的,他的私人畫室。走入畫室,他指了指天花板。我抬頭一望:鬼魅張著雙眼,詭異地瞪著我!
老師……我咬了咬嘴唇翻了翻眼珠。(根據我的仰慕者,我咬唇翻眼的時候,會燃起他們心底的烈火。)黃老師的目光遊覽了我的臉:“老師的畫作你不喜歡?”
古老的風扇,黑白在它身上撒。牆頭上,幾種彩澤在跳舞。
黃老師取了彩油瓶、顏色盤子、畫刀、上光油等給我介紹油畫的主要材料與工具;解說油畫的主要技法。“作為一種藝術語言,油畫的造型因素包括色彩、明暗、線條、筆觸、質感、光感、空間、構圖……”他翻開畫卷,給我說哥羅、畢加索、維納絲得米羅等,現代與古典油畫家所呈現的不同風貌;再舉自己的畫幀,展示油畫美。
美術這門學問,怎不叫人聽出耳油?
黃老師說得起勁,我完全著迷。突然,他把我的指頭握了去,貼在眼前望:“來,我看看你的指紋。”“你有十個陀螺,好漂亮的陀螺。我就知道你一定有著跟我一樣的陀螺!”他帶點興奮地說。他握得很緊,他手心熱熱的。“陀螺?”“嗯,就陀螺呀!你看你的指紋,橢圓形的一圈圈,很漂亮,像陀螺。”奇怪,老師怎麼突然看起指紋,說起陀螺。
“有陀螺的人有著別人沒有的藝術天分……”終於,我明白黃老師看指紋的用意。他想說,我們有著天生的契合?
黃老師靠得離我很近,他說話時有意沒意地把呼吸噴上我的耳垂。我的心亂了,這麼亂的心情怎麼作畫?
——可憐,我一直以來學畫的夢想,輕易地瓦解於這男人的面前。
阿黃。大概第三次學畫時,他讓我別再叫他黃老師。後來,後來的某一天,他把油彩彩在指頭,遊走在我的身上。我的心懸了起來。啊,我不再是個小孩,對愛慕者的愛戀無動於衷。阿——黃,我不太習慣這樣稱呼黃老師;但無可否認,阿黃他已經把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圍中。我低下了頭,他迫切的手勢忽輕忽重。他的指尖,有意無意地拈了我的腰我的腹我的臍、我的胸,挑逗著乳頭……
我不敢動,我連氣也不敢籲一口。一掠顏色飛上了白色的薄衣,彩色陀螺驚醒了沉睡的火焰。
阿黃把我載往一所偏離大學的獨立式小洋樓:“你搬來這裡,好不好?”“為什麼?”“這裡,我們可以安靜的在一起呀,就我們兩人。另個住客,不常在的。”“可是,可是我怕呀!”“怕什麼?”怕在一個人的房裡孤獨?怕在男人的烈焰裡成灰?我沒有回答。
後來,我還是搬了進去。或許火焰已經不能澆滅。
房租由阿黃繳付。屋友不在的日子,阿黃一定伴著我。只是,搬入小洋樓的那天,我下意識地感覺,阿黃或許已有家室,有一個妻,因為某些原由,並非時刻在他身旁。
“小玉!”“怎麼?”“我載你到附近海灘去!”“下次嘛,剛搬好,好累哩!”雖 然超愛大海,半日的搬遷我可累透了,推辭著。阿黃堅持帶我看橙黃色的浪花,強行把我拐了去。炎陽墜入地平線的那刻,拍打著岸的浪花格外迷幻。迷幻的浪潮一
拍拍,瞬間給黑夜姦污。阿黃摟著我回到車以後,並沒有把車開駛,而是從他的車座,跨來我的身上。他把我的車座調到最底,我的心澎湃著:這……
阿黃的車鏡畢竟是墨,窗外黑夜早摧殘了光亮,只有星星微弱地眨著眼睛。我的四肢微微發抖,阿黃攬著我,緊緊地。他的呼吸重重的,急促的。阿黃粗獷地,汗水濺上了我的身。
阿黃在我的脖子上了紅印。我呻吟著,他吮吸了我的手指頭,燙的:“小陀螺啊,我從來沒遇見這麼貼近我的你!”他的聲音滾沸著,有一股熱情,有一股幽怨。
幽怨?為什麼阿黃的熱情,夾帶著幽怨?他從來沒說,我從來不問。我們像水漾成無限的纏綿,一日日……
一直到阿黃給我遞上鑲框畫那天——
鑲框畫中,女人散著髮,嫵媚地躺在沙發上,男人的胸膛。男人粗糙的手,溫柔地擱放於女人豐腴白潤的乳峰。
阿黃在我的耳際,低吟著。小玉,你是我一生最漂亮的藝術!你讓我做了最艷麗的夢……他的呼吸,投射到我的身上。他的手臂,迫切地要求了我的腰身。
——等——我——
阿黃,走了。
溫習著他的摟抱,我瘋了似地笑。男人的喘氣聲沉重的、四面八方地,傳來。
我想起母親夜盼父親的歸來。窗外是夜的沈黑,窗內是無甚聲響的寂靜。母親的臉上漸漸消殘了顏色,如院裡凋零的花瓣,沒有色澤。
或許,或許我應該如阿行所說,搬離這所房子。或許我應該跟那些同齡的、近齡的,哪一個愛慕自己的男子,好好地譜一首戀曲。
我把陀螺溜在舌尖上——轉。牙齒猛力一咬:陀螺,毀了。
鮮紅的——陀螺。
原載: “2009年丹斯里鄭福成杯徵文比賽”得獎作品-季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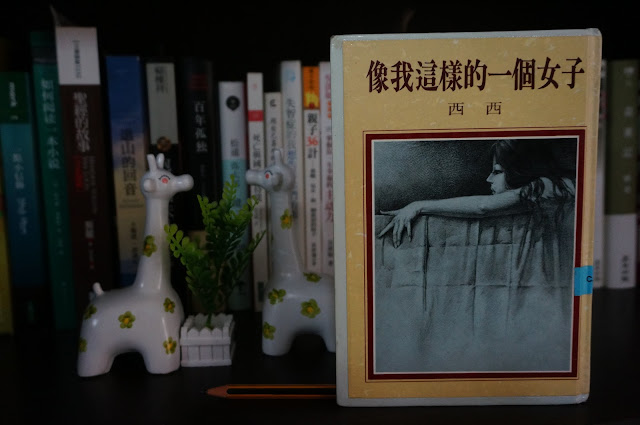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