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樂
 |
| 图:摄于巴黎卢浮宫 |
‘咔嚓’。照相機捕獵和氣團團的一幕:一家十口,笑容燦爛、眼神一致、嘴角上揚,溫馨甜蜜的全家福。
“嘿嘿,真好看,遲點我用Photoshop搞一搞,印給你們一人一張!”我看著數碼相機熒幕所顯示,剛剛攝下的全家福,興奮地說。三姐立刻嘲諷我每次光說說,結果千年都沒打印出來。
“哼,我這就去搞!”我不服氣,溜進房間,把照片傳送到電腦。門外隱約傳來母親斥責三姐的聲音:“嗨喲,大年初三,搞什麼搞,一起多聊聊不好嗎?”……
*
十三歲那年,我在母親的澡房裡,拿她那支防賊用的長長竹子,搗盲天花板上掛著的燈眼。母親刮了我一巴,我的臉頰紅紅地留下了四根手指的痕跡。狠狠地瞪著母親,我沒有哭。母親於是從天井裡的藤條堆中抽出了一支藤條,橫掃我的腿:颼颼颼颼!我站在那裡,僵硬著身體,腿一動也不動,眼睛冷冷地瞅著。母親把藤條丟
在地上,再次舉起了手,要往我的臉多刮一巴。父親站起身,把我拉到他龐大身軀的背後。他的汗酸味,刺激著我的鼻尖。
“你不要這樣!”父親對母親說。 “孩子還小,不懂事。”“不懂事不懂事,你是說我不懂事吧!她做什麼,都有你護著!”母親漲紅著臉罵。她的手,突然往自己的臉上刮了一巴:“好,是我不對,都是我的錯!”母親哭了,我楞著了。
父親拉著我的小手,握緊在他厚厚的掌內:“乖,到房裡做功課去!”我依父親,入房。房內有一張婆婆留下的,檀木製的古董雙人床。父親說過,那是婆婆來南洋時,一起運來的。雙人床上,大姐和三姐的小枕頭並排著,三姐正趴睡在
那裡;雙人床下,洋灰地上墊有一張三合板,板上,我和二姐的枕頭,列著。雙人床的床頭與右側,倚牆。左側留有一條小小的長型空間,向門。床角下是一張長長 的矮桌子,大姐和二姐妹坐在那裡,溫習功課。
走到大姐和二姐的身旁,站著。瞪著釘有鐵絲網的窗外,晃著綠身的芭蕉葉。然後又把視線,移至窗戶上端,漆白的牆頭上,架著眼鏡的,婆婆的臉。婆婆對著我笑。
從我走進房的那刻,二姐和大姐始終把課本,幾乎貼著臉地看。父親和母親爭執得激烈。每次他們爭執,我們都不說話。我從來不喜歡這樣的喧鬧與沈默的對立。我寧願和大姐三姐鬥嘴,然後讓二姐當和事佬,最後我們彼此做個鬼臉,繼續歡笑。
那晚,我在睡夢中,聞見父親的汗酸味。他抱著我,拍著我的背說:“乖,以後要長進,知道嗎?”我點頭,笑了,甜甜的。汗酸味不臭,反而夾帶著幸福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住在大山腳的姑姑和姑丈,來到我們家。我起床的時候,母親叫我快把睡衣換掉,到廳裡去。姑姑看見我,摸了摸我的頭,親了親我的臉。我覺得很彆扭。我與姑姑從來都不熟悉,為什麼她故作親暱?
父親的臉色,塗有一層灰。母親拉長著嗓子,堆笑對姑姑說:“唉喲,這趟真是麻煩你了!以後有什麼事,你給我們寫信通知就是!”
然後母親把我的手,握放在姑姑的手上。她把一個大背包,一併交給姑姑。
“有急事,你們可以用公共電話打給我。”姑姑把電話號碼寫在紙上,遞給父親。父親接過紙張,小心翼翼地藏進他破爛的錢包裡。
不詳的預感湧上,我的心,忐忑著。
“以後你就跟姑姑去吧!”母親對我說。她的語氣,第一次那麼溫和,溫和得我的身,起了雞皮疙瘩,想哭。父親始終沉默,一直到坐進姑姑與姑丈車的那刻,我對父親開口說一句話的迫切希望,最終落空。
我像一個棄嬰,被收留者帶上豪車,開了七小時,方抵達一個叫大山腳的地方,遠離家人。長達六年的時間裡,我沒有再踏足自己的家門,一步。
也好。我不必再跪於神主牌前,脖子掛上寫有'壞蛋'的紙皮,用手扯著自己的耳朵,懺悔度夜。也好。我不必再為不小心砸破了碗,負上魔王的罪名。母親的儲蓄箱裡少去的五塊錢,不會再是我取的。沒有人會再叫我小偷。而且,而且如果我是霉運的傢伙,那我走後,母親買萬字,就不會再和得獎號碼擦身而過……
姑 姑的房子,兩層樓高。門前有一片花園,種有大花圃。花園裡有一個旋轉樓梯,可以直通二樓的陽台。牽牛花從陽台一直攀藤到花園裡的白色藤架上。我和姑姑姑
丈,坐在藤架下的木椅,享用三文治火腿鮮橙汁與青葡萄。那常常是周末的晨,花香和黃鶯的歌唱,我一度以為自己在夢中。夢。
如果我是棄嬰,被收留在這樣一個童話房子,我想我的運氣其實不太壞。只是後來,我發現自己真的寧願,這裡的一切是一場夢。夢醒,我邊啃著麵包,邊和大姐二姐三姐,坐在天井的地上,把母親削好的竹,穿進父親釘好的藤架,以燒燙的方式定了型的鳥籠身。
週日上課,同學指著我為家裡制好的鳥籠染色時,染上橙黃的手指嘲笑:骯髒貓!放學回家,母親指著桌上的鹹魚腐乳與番薯葉說:“粥煮好了,快點去吃!不要吃到慢慢的,以為可以偷懶少做一點工!”夜裡,房外傳來父親和母親的吵架聲。我和二姐低著頭側著身,小心翼翼地鑽進雙人床下,躺在三合板上。聽不見聽不見!我們聽不見房外的吵鬧聲。我只聽見二姐給我說,一本又一本外譯小說的故事:《傲慢與偏見》、《飄》、《大地》……
姑姑的房子,走三步可達綠油油,一望無際的稻田。稻田的遠處,有火車的軌道穿越。夕陽西下,我總蹲在稻田前,聽火車的聲音。火車鳴笛的時候,我問火車,你遠遠地往哪裡去?可不可以把我帶返故鄉?
——而上地理課,我知道,馬六甲是唯一沒有火車穿越的州屬!
姑姑和姑丈以英語和廣東話交談,但是他們對我說中文。姑姑和姑丈和藹親切,關照我的生活起居。除了中文,數學英文或者科學等課業不明白的地方,姑丈都會在放
工後給我補習。姑姑給我做很多好吃的食物,還有一些沒見過的糕點。週末的下午,姑丈總帶著我到球場去練球。之後回家洗澡,再領著我與姑姑到餐館吃名貴的中 西餐。有時候,我們也上電影院。
我第一次跟著姑姑姑丈往電影院時,對著好大的熒幕合不攏口。電影的劇情似乎很精彩,姑姑常常拍著姑丈的手臂笑,或者輕輕地用紙巾擦鼻涕眼淚。而我,看著看
著,總會不小心回到小時候,房裡床前的那張矮長桌上,用我的紙娃娃踢三姐的紙娃娃。三姐大發雷霆,我很得意。大姐瞪了我們一眼,二姐就說:“功課做不完咯!”然後父親剛好敲門,我們飛快地把紙娃娃藏在課本底下,正經八百地握著筆,斜著頭蹙著眉,作一個認真思考的樣子。
姑姑和姑丈,從來不吵架。他們交談時都像壓低著嗓子說話,不留意絕不會聽懂他們在說些什麼。家裡總是很安靜。很多次,我想開口問,問我的父親怎麼樣,我的母親怎麼樣,我的大姐二姐三姐怎麼樣,我什麼時候可以回鄉,但始終,我把話吞回肚子去。
我在學校,不說話。除了老師點名問答時,我都不張口。有一次,上華文課,老師給我們現場寫作。呈堂批改以後,老師把我們的文字,挑了五篇為典範念出。念到我的文字時,同學們一貫洗耳恭聽,我卻在半途衝出課室,躲進洗手間,狂哭。
“十三歲那年,我在母親的澡房裡,聽見她和父親在房外的交談。本來我沒有留意,因為花灑的聲音,淅瀝瀝的,像雨在歌唱。我,正陶醉。後來我聽見母親提及我的名 字。我把花灑關上,豎立狗似的耳朵,聽。我想知道,為什麼母親特別討厭我,處處針對我。我沒有聽見答案。我只聽見母親,請父親把我這個不祥的東西送走:魔 鬼!見到我就覺得厭惡!
我聽著,我的眼睛變成花灑,淅瀝瀝的。我,願沉醉。鏡子裡,和母親長得一模一樣的臉孔,憎恨地望著鏡子前,母親的孩子?——母親說,自己的女兒是魔鬼。
十三歲,母親澡房裡的燈眼,瞪著我嘲笑。我拿母親那支防賊用的長長竹子,搗盲天花板上,叫人厭惡的燈眼……”
文字的上半段,大概是這樣寫著。同學說,有趣。我覺得,可笑。原來我的生活,有趣呀,有趣!
日子如常地過。有時候我很懷念家鄉,有時候我厭惡遺棄我的命運——不要我的母親,不保護我的父親。但命運其實沒有遺棄我,姑姑和姑丈,用著他們的愛,撫育著我。
十九歲,我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SPM政府考試,申請獲批進入大學。得到申請信的那天,我握著信件,突然想起了夢中,父親摸著我的頭說:“以後,要長進。”我的腦袋很重,重得有點昏暈。而姑姑接到了一通電話,自我的家鄉。
*
醫院的長廊很長。走入病房,母親穿著青藍色的病服,躺在病榻上。她的臉很蒼白,蒼白得像紙一樣。六年不見,除了不知何時爬上她臉的皺紋,已經被染了銀白的髮,母親沒變。母親合著眼睛,在睡覺。兩個窈窕的女生站在床邊,一個坐著的,是大姐。大姐沒變,只是比以前更漂亮了,頭髮一直系到腰間。站著的是二姐和三 姐吧。六年來二姐怎麼沒有長高?還是小巧玲瓏,三姐可就比她高了。三姐的皮膚很白,身材發育得很好。而我,竟然比她倆都高。
我站著,不知道要說些什麼。臉頰濕濕的,手顫抖著。我覺得自己就快要崩潰了。我們沉默著。父親呢?
趕回家鄉的途中,姑姑終於讓我知道,母親懷孕我的時候,是龍鳳胎。生下我和弟弟以後,母親扎了子宮,節了育。而兩個月後,弟弟夭折。
夭折,夭折。姑姑說到這裡時,我喃喃地重複著這個野獸的名字。原來我有一個弟弟,原來夭折曾經禽著我弟弟的腦袋,殘暴地,瘋狂地——咬著,舔著,啊,弟弟的血液,淋漓!
“姑姑,你騙我,你騙我!不要編可怕的故事騙我,不要!”我多想止住姑姑的話語,我多希望姑姑說的不是真的。但我,只是雙手緊壓著頭,緊閉著眼,沒有說話。
姑姑又說,婆婆逼著父親納妾,母親不願意。婆婆不斷地嘮叨,母親要我們張家絕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母親大逆不孝……父親始終沉默,沒有人知道他的腦袋裡想些什麼。後來,每逢父親出外坡賣鳥籠,母親總會看見父親躺在另一個女人的胸脯上。女人抹上濃濃的胭脂,嬌媚的,淫蕩的。別過頭,她換作一張歹毒的臉,問母親道:“看什麼看,收斂你兒子的屍體去吧!”而我,就在那時候,淪為母親口中克死弟弟的魔鬼。
“你媽變成這樣,你爸多少有些自責……”
難以置信。是夢吧?告訴我這是夢。夢醒,我又回到我的家園。父親釘著鳥籠,母親削著竹。我們幫著父親母親,為鳥籠染色上光油。
母親安靜地睡躺在病榻上。她蒼白的臉色,看不見怨,看不見仇,看不見恩,看不見愛——都看不見。母親,母親不是被摒棄的婦人。母親是一個美婦人,她沒有罪孽。父親沒有受妖婦的誘惑,沒有!那肉體鮮鮮,那狐狸精,她的影,是母親的幻!而我,我不是,我不是家裡的剋星……
“你記得以前媽媽會沒有事情自己跟自己講話嗎?”大姐開腔。“嗯。”我回過神,聲音半含在口裡,回應。我努力地,用盡力氣狂攔著心海氾濫的淚。
“你走後,她更常這樣。”大姐繼續說。“而且還會在屋子裡一直走來走去。有時候她會突然間抱住頭,哭到很像給鬼上身那樣。爸爸只是每個星期溜出去半天,其他時間都在家里安靜地工作。我們家的鳥籠生意,已經很糟糕。現在已經沒有人喜歡養鳥了。要養,也養電子鳥。”
“前兩天,媽媽又和爸爸吵架,吵架當然是因為媽媽又無理取鬧。後來爸爸就去沖涼,出來的時候,發現媽媽躲在房裡,把整罐清洗劑吞進肚子了……”大姐的聲音很平靜,平靜得像在敘述著其他人的事。而二姐,則在這時打岔:“醫生把一條很長的管子,從媽媽的鼻子,一直塞到腸胃去……”她哽噎著。
父親在這個時候走了進來。他手上拿著鮮花和水果。我們的目光交錯時,空氣好像凝固了。我的心往下墜了千里深。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
年初一。屋外的鞭炮是那麼的響亮。
我給母親倒了一杯開水,讓她和著藥吞下。母親吃這藥,有四年了。她的情緒不再有極大的起伏變化。待會兒大姐和大姐夫,會把小凱帶回來,可熱鬧呢。二姐在沙巴
的夫家,要初三才飛回來。三姐大清早就溜去阿盛的家拜年了。我說三姐你呀,今年底結婚,明年就在那里當媳婦了,急什麼急。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我想起了小 時候,我的紙娃娃把她的紙娃娃踢壞時,她氣著的模樣。
而我,剛念完四年的工程系。戴著四方帽的照片,父親前兩天剛把它掛在牆上。我從來不喜歡工程,最後卻選擇了工程系,完成了四年的學業,並且找到了在大公司里當工程師的職位。不要問我為什麼,很多時候,我自己也不懂。
多兩天見了二姐,我就要趕去檳城,給姑姑和姑丈拜年呢。嗯,父親把戶外的水梅盆栽,搬放在客廳的角落後,母親總算從房裡走了出來。她穿著我給她買的新年衣,問父親好不好看。“你穿什麼,都好看!”我第一次聽見父親,說蜜糖的話語,母親笑得眼睛都瞇起了。水梅的芬芳,瀰漫著整個空間,沁到我的心底去。我拉著父親和母親的手說:“走,我們拜年去!”
走出廳,關上門,我回過頭,對著房子痛快地喊:新年快樂!
原載:《我的父親母親》文學創作獎專輯-季軍\光華日報\2009.06.20--2009.0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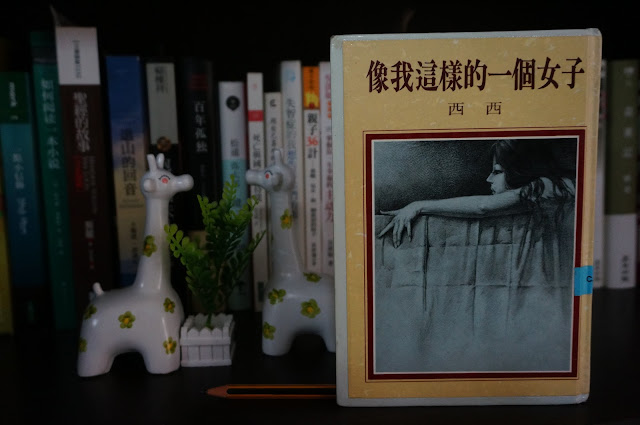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