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瑟林明(关丹林明,Lembing, Kuantan)
人家说的。到了一个年纪,不管男的女的,闲来没事就爱躺在时光的摇篮里,任它摇啊摇地,把自己带返昔日的时光沉沉缅怀。我有些苦闷。我离这把年纪大概不远了。我矮矮的身子踮起了脚尖,小手伶俐地自玻璃罐子掏出一把“Hacks”糖果,去了橙红色的透明糖纸,一口咬碎,自个儿也很高兴。还有还有,还记得两毛钱的红豆冰棒吗?
我心中一动,正巧有个皮肤黝黑的孩子从对面街跑来。他眼睛乌溜溜的,伸手抓了一包陈列着的零嘴,猛然意会到我的注视,便歪着脑袋看了我和伴侣一眼。我微微一笑,他裂开嘴来露出带黄的牙齿,少了颗门牙。他买了零嘴,一溜烟奔了出去,临走前不忘回过头来多投望我们一眼。
“要不要买包瓜子来啃?”我建议。“好呀!啃瓜子除了要有兴致,还要有这种难得的闲空!”于是,我和伴侣就坐在杂货店外,一张褪色的小凳子啃起瓜子来。
那是一个周日的午时。林明好像一座空城,一排排朴素的木板屋,门几乎都是闭着的。仅有的小油站贴上了停业的字条。唯一一条不长的大街,老榕树落叶萧萧,衬托着没有行人、分外安静的街道。偶尔有隆隆的摩多声,从对面巷子传来街上,再由街上回到对面巷子——是友族同胞的少年人兜着风儿做游戏。
我和伴侣聊呀聊地,不知过了多久,传来重重的吱呀一声木门声,隔壁一家店铺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穿白色汗衫背心的老人。老人大概一看即知我们是外来者。他向我们点个头,随即聊了起来。
“林明的油站今天没开吗?”伴侣对林明的微型油站很感兴趣。
“事头死咗,无人做野,早执笠咗咯。你要加油?到出边大路旁买呀,有卖一樽樽嘅,自己加。”老人用粤语回答。
“林明怎么好像一座空城呀?那些店铺怎么都关着的?”
“人一个个死噻咯!店铺也关咗。后生仔边个要留响度啦。”老人说到这里,我觉出一股凄凉的味道。
“我哋响度等死。”他的眼睛,遂寂寞了。
“后生仔重留响度做乜野啦?政府都咪制依块地呢,你哋要,摞去啦。每年都浸水。十年前浸到顶。病咗都冇医生睇,病咗要到关丹睇。”老人一说,便停顿不下来。他说起从前,还是年轻力壮时,是林明锡矿场的矿工。那时候,林明拥有世界最大、最深的锡米矿场呢!矿井最深达1,600公尺,每一层距离30公尺,整个广场全程将近322公里。矿场雇用的工人,更是高达1万5,000人!
恍惚间,我们仿佛随着老人,回到林明因矿业而辉煌的鼎盛时代。一晃神,林明繁华热闹的景象又消失了。80年代,锡矿价格大落,锡矿业连同林明悄然隐没。现在的林明只剩下2,000余人,都是老人和妇孺啊。想象林明的热闹,真叫人惆怅,旧事如烟。
老人的眼睛不是很清楚,有一点灰灰的尘。他自称为寡佬,和林明大部分的老矿工一样,把一生的青春贡献给锡矿,没找到配偶。锡矿业没落之后,他们年纪大了,且不富裕,婚姻大事只好悬空。
告别老人以后,太阳下去了,天色昏蒙。
山镇下起绵绵雨,带着寒露的气息。街灯下,只有一家餐厅在营业,煮厨白发稀疏。我们带着悬念品尝林明茄汁面:面条是自制的,比一般黄面细,但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茄汁汤上面覆盖着肉碎虾仁,和着面条一起咽下,味道还真不赖。捧菜的是个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会是林明面的继承人?
回到民宿时,门上了锁,叫唤无人呼应。我们面面相觑,拿着登记入住时领的钥匙,当起民宿的一日主人。民宿内挂着一些昔日繁华的街景,和2000年大水把林明一家会馆淹没顶的照片。伴侣打趣问道:“这里不错呀,很悠闲,度假可以呆多久呢?嗯,一星期吗?”
“不了,最多三天。”我撇着嘴说。
伴侣觑看我半晌,笑了。只因平时我心心记挂和平幽静乡村,念念盼望能种菜养花。
滴答滴答,雨淅沥沥地打在屋檐。透过窗从楼上望去,街心无人。民宿对面的店铺前,凳子上陆续坐了几个老人,花白的头,彼此是多么可亲!展开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个漫漫长夜,同伴们逐一离去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
《星洲日报·星云版》2011-1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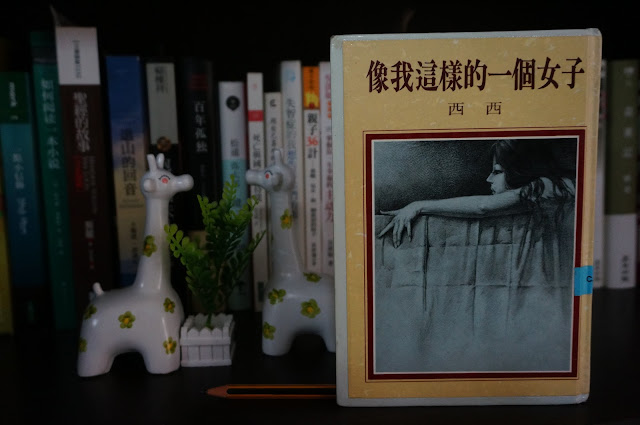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