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鬧鐘
从七岁上学那年,爸爸就当了我的闹钟。清晨六时许,他在我的房门外喊道:“欢呀欢,醒来咯,起床咯,上学咯!”除了周六和周日,他每天都是这样把我唤醒。我发现当爸爸真的不简单,不只要比孩子起得早,还得为孩子备早餐,至少我的爸爸是如此。我的早餐很简单,那是一杯热腾腾的美禄饮料,和三片涂上植物油的白面包,十年如一。这样的早餐我吃了十一年,却从来不觉得腻,至今仍然很爱美禄和面包。
后来,四姐给我送了一个公鸡形的闹钟:血染的冠头,锦作翎;昂昂的气象,羽毛新。闹钟是陶制的,栩栩如生。只要把时间设定好,时辰一到,它就会朝天喔喔啼。第一声响主人醒不来,它顿了顿又继续啼叫。我爱公鸡闹钟,却很少让它啼叫,因为我更爱我的幸福闹钟。
十九岁那年,我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升学。从此回家的日子总是短促,爸爸不忍再当我的闹钟,总要我睡晚一点。
初时在外生活,我有一个睡得很沉的室友。她有一个大闹钟,闹钟的头上有两个半圆形的小铃铛,好像两只耳朵。在两只耳朵中间,是一个能左右摇摆的小铁锤。每当到了室友所设定的时间,它就开始敲打耳朵,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声音,并连头带身地震动。室友总是一次次地按下闹钟按钮,不愿醒来。铃声响得久了,房里的墙壁和地板仿佛也都震动了起来。起初我总是很快地跳起身,把闹钟的按钮按掉,然后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把室友叫醒。后来我觉得累,便尝试不理会。而室友总是听之不闻,逼得我非投降不可。那时候起,我患上了“闹钟铃响恐惧症”。
需要设定闹钟时,我的生理闹钟总会极力配合,以数秒之差,响在闹钟铃声响起前,唤我把闹钟按钮关掉,避过高分贝的声音。再后来,手机的闹钟功能替代了闹钟。虽然手机闹钟的铃声,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挑选:或是悦耳的音乐,或是不太折腾的铃声,但我对闹钟,始终很有些厌恶。
多年之后,有一天,我乘上了飞机,越洋到彼岸当起临教。久违了上学时大清早就得起床的日子,晨起真叫人懊恼啊!我在彼岸没有交通工具,上学乘搭校车,五点半就得在住宿处候车!
上班的第一天,清晨五点钟,手机响起了——咦,是伴侣越洋拨来的电话。“我给你当闹钟!”伴侣说。但觉一股暖流,涌上心窝,睡意便给驱逐了。伴侣告诉我,这对他没有太难,因为他醒后,很快又可以入睡。然而,我的内心还是暖呼呼。接下来,就有点出乎意料了。数百个日子以后,今天的今天,每一个上班的晨,我还是接到伴侣拨来的电话:“起床咯,上班咯,不要迟到哦!”
有人说,熟悉会让人麻木,麻木会让人误以为身边人为我们付出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以为爸爸或伴侣当我的幸福闹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那些迷梦中温暖的叫唤,是我一辈子戒不掉的幸福。
谢谢你们,我的幸福闹钟!
(“哎呀,怎么办,以后你要怎么给我们的小朋友备早餐?”伴侣捏了捏我的鼻子,问道。)
《星洲日报·星云版》2012-0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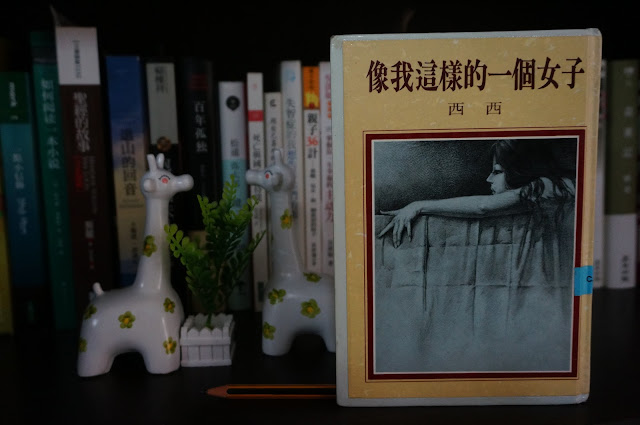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