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的門板不聽話
太阳滑下了天际,回教堂传出Maghrib的祷告声,惊醒了黑夜。我估计,六十分钟过去了,紧闭着的门板始终漠然。我蹲下来,把左脸侧靠着地面,偷窥门缝外那一点光。那里有一群蚁,来来往往地搬东西。它们来去自如,真叫人艳羡。
“开门,开门哪!有人被困在这里!”
没错,我呼救。回应我的却是凄然的沉寂。坐落于角落间的公寓单位,离人来人往的公共长廊很有些距离。何况浴室与公共长廊间隔着一间储藏室,这样的呼叫,徒劳。
“喂,我被困在十八楼公寓的浴室里,你能不能......” 拨电求助是痴想,浴室里没手机。六十分钟前,室内的空气还是滚烫着的,它被太阳光灼晒了老半天。要不是那车龙不听使唤,要不是尿道备受压迫,未痴呆而几近失禁,那时候的我应该在厨房里,迎着窗外残余的亮,洗菜炖汤煮饭。而现在的我,应该正大口大口地享用着我的晚餐。
呼——怎么办?
我在浴室的地面躺了下来。不久之前我耗尽力气地洗刷地面,看来绝对明智。我的胃开始鸣叫。我动得了腿,却转动不了门把。我动得了脑筋,却采取不了行动。玻璃窗的位置很高,高得我踮起了脚尖,亦无法把窗外探个究竟。我跳呀跳的,要不是来不及弄明白就被困在浴室里,至今我还不知道窗外是直通低楼的空穴空间。十八层的高楼,只有蜘蛛侠才有胆识攀爬吧!
室友外出公干,已经两天没回来了。他往往一去就是六、七日,我很难对他能施于援手抱持乐观的态度。一股寒意涌上心头。平时我最喜欢在此泼水又唱歌的浴室,突然成为了我的囚牢。我的听觉霎时间变得灵敏异常,每当远处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我便神经质地大声呼救。而回应我的始终是没有人。
我估计,又过了六十分钟。或许,那更长。
我疲惫地坐起身,在漆黑里。我不敢让眼睛闭上,要是睡梦中室友回来,走进他的睡房并把门关上,那么我‘逃狱’的机会很可能稍纵即逝。就在这时候,我再次听见了声音。不知是楼上还是楼下,传来淅沥淅沥的洗澡声。我像极了疯子,兴奋地拿起绑着刷子的长棍,拼命地往屋顶敲击呼救。没人理会。我又把木棍往地面击打求助,亦没人回应。我彻底的失望。
黑暗中我再次陷入了寂静。全世界的光亮与声音,已离我而去。我舔了舔破裂的唇,喉咙干涩。我需要在这里呆多久呢?是一天、两天,还是更长?大地震受困的难民,喝尿尚且能保命,要是室友数日不回来,我顶多喝自来水来填肚子。我比灾民幸福。不对,室友有时公干长达两周,喝水能抵两周命吗?我不确定。
我调匀呼吸,想念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妹妹。我闭上眼睛,默念着恋人的名字,千百遍。我祈祷着心灵感应。啊——还有我的朋友们呢,你们怎么都那么遥远?我把左脸侧靠着地面,往门缝外望。黑神捻灭了光亮,蚂蚁已不知所踪。走廊不再传来脚步声或对话声。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我听到了钥匙的声音!我的室友他......回来了!他听见了我歇斯底里的求救而回应了我!他试着从浴室外转动门把,门把转动不了。他试着拿铁锤来敲击门把,门把给敲了出来,门板破了一个洞,却推动不了,稳如泰山。他急了,我请他别慌,去找个开钥匙的技工来帮忙吧。他说十一点了呀,去哪儿找来技工呢!我说不急,不急。不知又过了多长的时间,他把技工给请来了。我听见超过两个人的声音。他们敲呀打的,转呀推的锯的,门板还是推不动!最后,他们请我站得远远的。“噼啪儿——”门板应声而倒。四个大男人干巴着眼站在我的浴室外。
“你没事吧?”室友问。
“没事。”我故作镇静,不听使唤的却是我受惊的魂。我越过他们,奔向阳台,泪水决堤。
《星洲日报·星云版》2012-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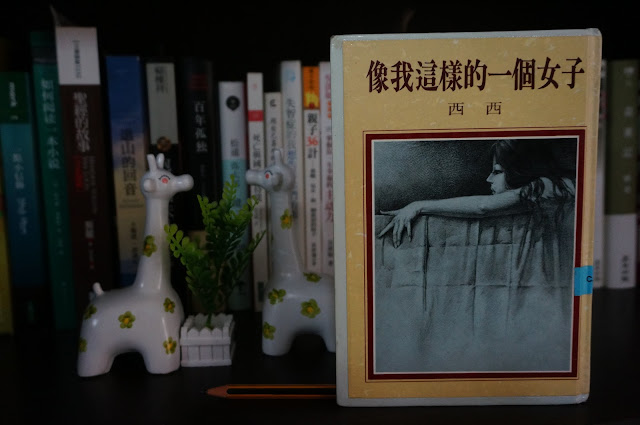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