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女傳
“你真的很像飞女哦!”研究所同学指着我一张波浪形长发、黑夹克上衣的照片,睁大双眼,提高音调叫道。我斜她一眼,捏起拳头轻捶她一拳。都拜陈老师所“赐”,给小女添此绰号。陈老师三十来岁,说话尖酸刻薄、一针见血。他怀才不遇,抑郁愤懑。身为旁听生的我,喜欢听他讲课时,穿插的灰色幽默。一天,他冷不防对准我问:“你是不是飞女?”我一时间怔住了。
我向哥哥提起这件事。没想到他说,美其名叫你飞女,实则指你粗鲁。我又怔了一怔。小妮子虽非温柔万千、水做的女人,但说到男人婆个性和举止,我可沾不上边吧。偏偏飞女这绰号,念大学时已另有老师给我冠上。那时候,学术研究乃原住民课题的我,先被该老师赋以一个原住民名字,人前人后“阿美娜,阿美娜”地叫唤;在台上发表设计报告时,我不经意把手插进口袋里,他瞪着眼问:“你是飞女吗?干嘛把手插在腰际?”——引来哄堂大笑,飞女成了我第二绰号。我拿该老师没办法,气得眼睛斜睨,嘴巴撅起。多年后重返校园,遇见该老师,两人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曾经耿耿于怀的绰号一事,早已不置心上,倒成为有趣话题的开端。
鬼使神差,如今陈老师重提“飞女”一词,我不再介意,只好奇地问起原由。他的回答是:原由?纯粹只是一眼看去,好像电影里重型机车上飞女的感觉。就像我给其他同学取的动物绰号……
翻出未曾褪色的记忆,我从小手指纤长,动作阴柔,思绪敏感。家人批评说:女孩儿也该刚强点儿,于是送我学习跆拳道。学拳不久,我即上了瘾,一直到到考上黑带阶段,也当了拳会主席。或许我体内流着飞女之血吧,一经触动则澎湃了起来。我想象前辈子自己是个女英豪,投胎转世后被降为飞女,云云。
女孩儿不是本该温柔些吗?——多年后问起父亲,他说那女孩儿该学习阳刚的话,绝非他所言。于是飞女之“冤”,似乎就断了头。
我发现我的跆拳道黑带阶段文凭,会让有些人显露惊骇的表情。我参加入学面试时,发问环节结束以后,两名老师拿着我的文凭,望着我的脸,面部神态好像我是个大魔头。其中一名老师还把椅子往后一挪,叫了一声:“黑带高手,我怕!”……入学以后,该老师替我在系上“宣传”。系主任得悉系上有个武打者,每每碰面,都问我是否还练拳。“哪来的闲空呀?”我苦笑。景观绘测系课业繁重,偷闲练拳像是旧梦版图,难以复活。忙课业的季节,我曾因晕倒家中而翘了课。老师关切我的安康,或问我武打女身体怎么如此纤弱,或劝我再忙碌也得抽空练拳。我的健康每况愈下,所谓的武打女形象,颇含讽刺意味。
工作以后,我报名加入了自由搏斗课:是结合武术、音乐与舞蹈的运动。重拾“武学”让我感到生命的欢悦,一些学员却领略不了当中的道理,申诉说教练“变态”,锻炼时让学员“丝毫没有喘气的机会”,参加了几堂课便退了学。
谁知道生命是一个幽默的玩笑家,一场脊椎矫正手术让我身体僵直、行动受限,许多运动不再能进行。只好告诉看官切勿多虑,飞女浪迹江湖,平复多场腥风血雨。既然武林已恢复安宁,飞女这就退隐而出,不问世事。
 |
| 生命是一个幽默的玩笑家—— |
《星洲日报·星云版》2013-0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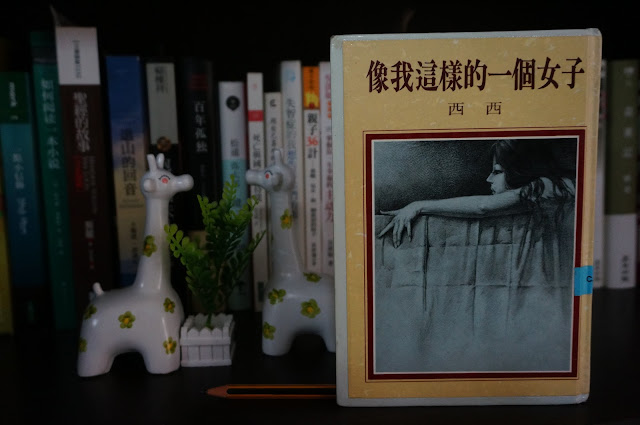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