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老
母亲的头发乌黑亮丽,牙齿整齐洁白。她的容貌,很难让人洞悉六十九岁的批注。年纪与母亲相仿的邻居早已齿危发秃,背部隆起一座小山,不拄拐杖的话,有些根本无法行走。母亲的不老传奇,让他们吞食了苍蝇,一口咬定她眷恋过去,白雪染青丝、齿落戴假牙不肯承认。母亲口头上埋怨他们诬赖自己不老实,眼睛却发出微妙的亮度。
哪里有人戴假牙还能啃甘蔗、吃坚果的?
我的头发如果染色,发根早就银白了!
我的头发如果染色,发根早就银白了!


 知道你年年十八,青春貌美啦!
知道你年年十八,青春貌美啦! 她这单调的话题,一再穿透孩子们的耳膜,唤来哥哥一句调侃:知道你年年十八,青春貌美啦!
母亲明白时光之轮飞速运转,笑得几近沁出泪珠。你们都三、四十岁了,我怎么可能十八岁?
除非滂沱大雨,每天,她跟着父亲一遍遍穿行在绿树成荫的河滨走道,英殖民留下的老房区,或古城门和大钟楼下那种富有情调的地方,被夕阳剪出老夫老妻偕行的美丽身影。快走使母亲身体年轻。一起去旅行,她疾走如风,比我们年轻人矫健。
母亲的手艺也很巧。量衣尺、缝衣针、五彩线、花布料,只要把这些裁缝工具及材料交给她,碎布就能拼凑成美丽被单,旧衬衫化身为布娃娃,有些嘤嘤哭,有些呵呵笑。童年对母亲一双手的印象,确实如同魔法。蓬蓬耐看的大纸球,火光映红的铝罐灯笼,椰叶编成的小蚱蜢……种种玩意儿,她都能信手拈来。邻家小孩唯有巴巴瞪着眼睛看,艳羡我们秀玩具的份儿。
 |
| 仅仅几年光阴,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升学、工作、组织小家庭,一个个离家去了。 |
仅仅几年光阴,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升学、工作、组织小家庭,一个个离家去了。曾经拥挤的居住空间,空落成偌大一栋老房子,留下父亲和母亲守着清冷。每逢假日和节庆,我们约好了一块儿回家,母亲老早就翻着日历,日子未到,已成了忙不迭的黄蜂,嗡嗡,嗡嗡。她一下打扫房间,一下清洗浴室。待我们到了家,她一会儿问:今晚要吃蒸鱼还是炸鸡?一会儿问:明早要吃金瓜糕还是芋头糕?如果换来冷冷一句“你要煮什么,就煮什么”,或是敷衍的答复“随便你”,母亲饱满的精神一定像泄气气球般,消了一半。
一时三刻后,她恰似从一场漫长的昏睡中醒来,悬在心上的问题再次浮现。我们的对答犹如蝴蝶从水面上掠过,一眨眼就消遁无声。母亲兴冲冲又举出同一些菜肴,让我们做选择。
一次,母亲的拿手料理,——纸包鸡的香气从我的记忆册中飘出。在姜汁、蜜糖、麻油等腌料中,浸泡了一夜的鸡翼,以纸包好,下锅油炸,纸包鸡呈金黄色,在油锅里滋滋作响、蹿出香气时,甭说吃,光瞧着、抽动着鼻翼闻一闻就感到痛快。我说惦记着这一道菜,母亲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是纸包鸡?
为什么要用纸把鸡翅膀包起来?
她的疑问,在我心中流动成复杂的思绪。后来我发现,母亲的健忘不单在于想不起纸包鸡这回事,做菜她不无错下两次盐的时候。万一今天她移动了一盆花的位置,隔日她找不到的话,父亲就得随着她翻转在院子里。
 |
| 每个人都会变老,我却忽略母亲老了。 |
岁月悠悠,每个人都会变老,我却忽略母亲老了。
有一天,母亲拉着我的手,移动在她手背上说:你看,你看,我的手皮可以捏起来了,跟你们小时候,阿婆要你们捏她的手一样,你捏一捏看吧!
我不愿意,母亲径自示范给我看。她捏起手背上皱褶深深、松驰无弹性的皮肤。那皮肤好像橡皮带一样,远远地向外伸展,放手后约莫数秒,它才恹恹无力地下滑。我望着母亲,偷偷把惆怅屏在心底。
我以为母亲不会老的,可是她老了。岁月不但吞噬了她的好记性,也教皱纹和松弛的皮肤磨损她曾经的美貌。母亲的脑袋、嗅觉及听觉,一概隐隐荒唐起来。




母亲生活枯燥,我回到家,总见她闭着眼睛,歇在躺椅上听周璇、白光、姚莉及李香兰的歌声,穿透历史在厅内悠悠回旋。那歌声带有时间的况味,渐渐的,它与母亲细微的鼾声错落交叠。等到她从梦的彼端醒过来,她便弯下腰,把手伸到睡椅下,抓来一个罐子,打开四姐买的开心果要我吃。我吃了开心果,又抱来妹妹买的薯片,哥哥买的鱼饼,周而复始。
妈,你这么困吗?你梦见了什么呀?我问。
不困呀,没有事情做,怎么会困!母亲说。
我想,母亲要的不是坚果,不是糕饼,而是陪伴吧!我若有所思地嗑瓜子,母亲眼神专注地剥腰豆,溢出淡淡的香气,分不明是瓜子香抑或腰豆香。忽然,她停下剥腰果的手,叫了声“欢呀欢——”,我从沉想的状态中回过神,应了她一声。母亲告诉我,到了这把年岁,她很少发梦了,年轻时就经常梦见外公。她的眼神,随即泛起了温柔的涟漪。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只能从舅舅们的模样,揣想他干庄稼活儿的样子。母亲的记忆里,曾经,舅舅天天牵着她的手,带她到禾田给外公送饭。她总是热情地喊外公用餐。外公直起腰,手往裤子上擦一擦,去了淤泥,张开双臂,把她高高地背到肩膀上,母亲看到了辽阔的田野风光,她小手只要一伸,仿佛就能触及蓝色的天空。后来,外公到森林砍柴,森林的沼气把他年轻的生命夺走了。还是个稚童的母亲,不懂外公辞世是怎么回事,用餐时间一到,她便嚷着舅舅带她去田野找外公。
人生很长,也很短。记忆让我们留住些什么,也让我们失去些什么。外公早已永离众苦,年近七旬的母亲,不曾忘怀的却是她与外公同在的温暖记忆。
 |
| 我何其有幸,长长的路上有父亲和母亲的陪伴。 |
我何其有幸,长长的路上有父亲和母亲的陪伴。今儿,不老的母亲老了,对母亲的关爱,岂容蹉跎!
《星洲日报·星云版》2015-0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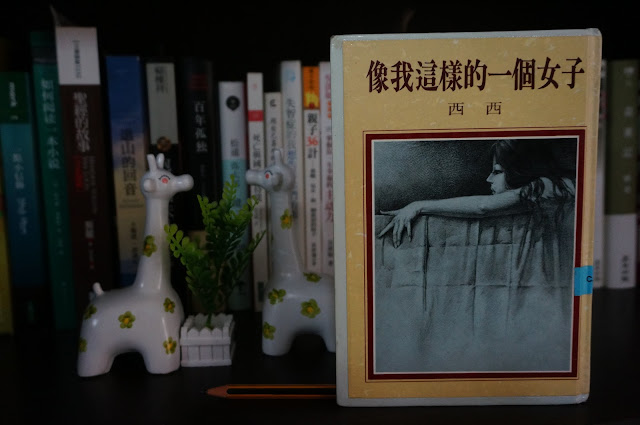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