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虫恨

从悉尼之旅起,我对臭虫的仇恨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臭虫是不好惹的,想到它,就要浑身发痒。
位于悉尼皇家公园对面的背包客旅馆,洁白的墙壁泛了黄,床单色点斑驳,食物的残渣也零星地散布在床脚下,灯光暗幽幽的。
“这么脏,要怎么睡呀?”走进去,我们都没有心理预备。
但是出游的人数多了,临时决定要更换旅馆,找不到横竖六、七个床位闲置的地方。于是,在那向晚时分,我们一心想着上哪儿找来服务员,粗略地清理一遍。最后,哥抓来塑料袋当套子,把床脚的烟头和躲在桌子隙缝的屑片一一除去。
洗浴后,人人身体倦怠,预备享有一段好睡眠。旅馆外,背包客却像吸食了毒品似的,大呼小叫起来。他们身上浓烈的酒味、缥缈的烟云和忽高忽低的喧闹声,透过窗户传来。
“一群魔鬼!”我听得心烦。
凌晨,蹑手蹑脚,魔鬼真出现了!
趁着夜黑,它们陡然闯出,把致痒的唾液像涂牛油般,涂抹在我的皮肤上。我从五指的关节、手肘、胳膊到脖子,都感到奇痒。哥和姐翻来覆去,睡眠同样被什么挟持走了。是百虫疾走,从床的边陲地带扑上来,叮咬我们、吮吸我们的血液?
冒出这样的念头,我捻亮灯眼。灯光映照出来的小小范围延伸出去,痒的感觉减少了,视线所及的细节,也只是更多的食物细碎罢了。
姐夫和父亲的鼻鼾声节奏有致地响起来,高高低低,倾诉着疲困的情绪。撑不住钝重的脑袋,哥和姐也相继睡着了。
我只好把灯熄灭,魔鬼又作怪了!大胆向我晃来。“你们到底是谁?”我下意识发问,魔鬼无声无息,不肯作答。我诅咒它们,它们不被咒骂惊吓走。我搔痒,越搔越痒,痒得濒临发疯……
一夜,像一千年漫长。
我的眼皮,支撑不住合上了。人声喧哗逐渐远去,然后靠近,又远去。当天蒙蒙亮时,背包客酒臭的身躯已醉歪在沙发上。旅馆静如坟地,天地都躺下了,只有我挠着痒爬起身,就着窗口、借助天光,俯看自己的腿肚子。只见红痒一驼驼,组成浪,朝视线涌来。
“啊——!”我的尖叫声推醒了家人。
姐揉着眼睛含糊应答说,她的皮肤也很痒。她抓挠不断,打开灯,只见她脖子上浮现的红点,已饱满成一大驼痒。母亲起身,定了定神,拿眼神逡巡我的床。“喏,是臭虫!”她指着床单上琥珀色的肉点说。
臭虫?啊!这远在古埃及和古罗马时期就出现的魔鬼,它们曾经销声匿迹了一段时期,当时代把它们遗忘,赫然爆发了臭虫事件。臭虫的黄金时代来了。纵然清除了这个国家的臭虫,却无法清除盘踞在世界各地的臭虫。它们不识归途,喜欢躲进人们的手提袋或行李箱四处旅行。它们潜伏在旅馆、诊所、电影院等养成所,繁衍后代……
呼应着母亲的发现,有更多只臭虫出现在我和姐的床上。母亲两只指头夹紧它琥珀色的肉点,用力一捏,“噗”的一声,肉体爆裂了。
“去死吧!滚!”我发狠说。
太阳冉冉升高。捏碎的臭虫在床单上爆出红花来,色泽浓淡适中,气味新鲜,三朵,五朵。我仿佛瞧见一整夜,成群的臭虫恣意横行,在我们的床上游行。它们肚子平扁地钻进我们的衣里,肚子滚圆陆续出来。它们与我们的肌肤温存,以我们的血液充饥。我们身上新鲜血液的味道,是它们最渴望的上乘食物哩!
向我们挑战、复仇似的,被捏死的臭虫请兄弟来了。至少有上百只臭虫在我们的衣物上停留,贼贼地跟着我们,远远地到了玛利亚岛。岛上风冷冽,好在太阳也猛烈。我们把挂在肩上的小背包、扛在背上的大背包以及内里衣物全摆在太阳下晒。高温是臭虫的敌手。当阳光照在衣物上,阴暗的小天地里突出了红光,臭虫骂了一串脏话,奋勇挣扎逃出来。它们赶不及没入草丛就累了,覆在衣物表面干燥成标本。
被臭虫袭击早已是过去的事了,回想起来,那憎恶还是令人内心平静不了。
2016-05-13《中国报》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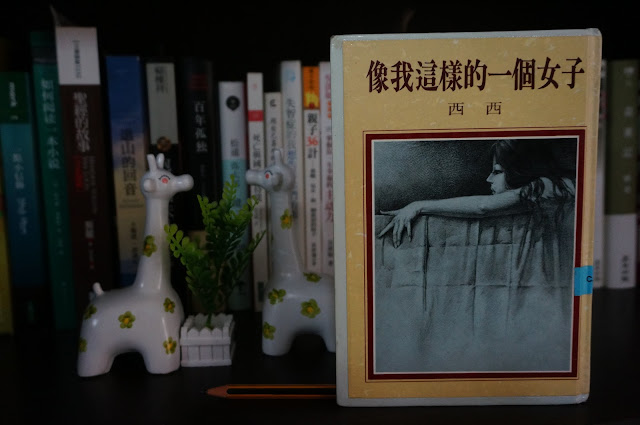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