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母校
我对母校有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不大好说。这间古老的华文小学,1922年就创办了。每当带着外地朋友到马六甲玩,路过校门,我就指着说:“你们看,这是平民小学,我以前在这里念书!”说着,眉毛扬了起来。
我们一家,我父亲,我四个姐姐,一个哥哥,我,以及我妹,都在这里念书。母亲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姐姐、哥哥到了入学年龄,她和父亲可是在报名日前一夜,就抱着矮凳去排队挂号,为孩子争取入学名额。“替你大姐报名那晚,下起了大雨,雷轰隆隆响个不断……”母亲记忆了一下,说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他们寄寓孩子们受了教育,将来走得更远、过美好的生活。
我初上学,又笨又呆的记忆,是很具体的。第一天上学,父亲找了一个座位,叮嘱我说:“坐这里吧!”哦。同座的她,是一个很高的女孩,眼睛很大,睫毛弯弯,笑容一若盛开的蔷薇。父亲走后,一群男同学在课室里跑跳,朝我的座位指一下,说:“虱子婆,你跟虱子婆坐!”他们都快乐活泼,好像早就结识了似的。
同桌的她,闭着嘴巴,闭得很是要紧。有个大个子忽然跑过来,朝地面啐了一口,挥手弄倒我的水壶。淅淅沥沥,雨落下来了,地下的蚂蚁在喊。我听不见,带着两只眼睛,看着同桌蓬蓬松松的头发,沉迷于当猎人的心无旁骛。虱子真住进她头上的森林了吗?虱子是什么形状的?我听到虱子的心脏在跳动——我想,我不喜欢虱子,我的头发是不给它们住的。
每天放学,校工都举起牌子,站到路口,张开双臂,把来来往往的车子挪开来,拦在左边和右边。一年级的小同学们极之神气,连奔带跳的,不管下午班主任怎么高喊着:“小心!小心!”一忽儿就闪到对面街去了。有一天,脚步声走完了的时候,校门口静悄悄的,整条大街旁只剩下我又矮又瘦的,独个儿缩在一角。我手足发凉,说不定父亲忘记,不来接我了。校工把大门锁上,走了。
“不回家?”下午班主任找着我。我抬起头来,看见黄昏的云彩泻下金光,落在他抹上油厚发蜡的白鬓上。他微笑看着我,和我并排站在一起,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说:“别着急,老师陪你等。”他也是我的音乐老师。他有慈爱的面容。父亲把我带走时,天光已黯淡下来。我一步一回顾,留下深刻的印象。
学校的侧门外面,有一个摆摊子的麦芽糖叔叔。叮叮当当,我喜欢看他用两块铁凿子敲出一方一方颜色晶亮的麦芽糖。星星点子四溅,空气里漾起一种甜,刺激着味蕾,一想到就分泌出口液。我眼睛直呆呆地望着那些麦芽糖。它们没有固定的形状,握在手中,含在嘴里,该是香甜直到心里去吧。口袋里的硬币挣扎个天翻地覆,想要跳出来,又被我押了回去。吃零食对身体不好,老师说。现在呢,我要到哪儿去寻那童年的麦芽糖?
从学校的大门进去,右边是二楼建筑,左边是候车亭。二楼建筑楼上开朗活泼,楼下严肃板正。课与课之间一有空档,低年级的同学就在课室门进门出,在梯上跑跑跳跳,远远瞥见纪律老师踏步拾级上来,吵闹声瞬间弱了,像猫蹑进课室。
候车亭最好的一角,掩映在一株老树的浓荫里,密叶间垂挂着许多裂开的荚果。风一吹,摇落满地海红豆,在阳光的照射下,赫赫如火。男同学把它们抓起来,养在玻璃罐里,藏进女同学的书包里,小心翼翼哩。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女同学发现时,被这冒失的举动吓了一跳。然后她说她讨厌走路像猴子跳的男孩子。她说她讨厌功课永远做不好的男孩子。她说她讨厌榴莲头式的发型。其实啊,一朵浅浅的笑容不自觉地出现了,——一朵无法隐瞒纯真秘密的笑容。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柔软滋润,弄不清自己了。这爱情最初的印象呵,似雾又像花。
吾华南殖历史长,荜路启炎荒,勤劳艰苦流血汗,美德宜发扬……
穿过二楼的建筑和候车厅,直走豁然开朗的是大操场。国歌在这里演奏,校歌在这里扬起,校长在这里训话。校长的训话是没有气味的,因此很难记忆,但我记得第一次在这操场的台上讲故事,紧张的情绪坐稳心房。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y named Jack……
眼睛。眼睛。眼睛。
到处是眼睛。
我无法将操场上集合的许多只眼睛串联起来,组成一副图案,就像戴着镣铐被押上刑场的犯人一样,眼神麻木,身子颤抖,也不知用鼻子、嘴巴还是颚骨,把故事以泄洪的速度倾泄完毕,一鞠躬,闪身下台,险些摔倒,逃离处决似的离去了。
大操场的前方,也是课室楼,右边就是新起的校舍了。别的楼矮,它高。别的楼衰老,它年轻。别的楼灰头丧脸,它明亮灿烂。五楼的它,耸立在当年的马六甲市,显然是个“巨人”了,可以眺望四周景致。新校舍底楼,下课时人声吵杂喧哗,冒着咸、辣、酸、甜,糕点和面食那些鲜呀香的气味,让孩子们一天比一天高。
食堂的楼上是高年级课室、图书馆和视听室。顶楼的露台承接阳光,风从外面呼呼透进来。同学们在那里上音乐课。一面唱歌,一面望向蓝天,幻想下一首歌唱完,风声、歌声与轻轻击撞时三角铁发出的叮叮声已把天上的仙女请来,身披彩衣,翩然起舞。在那里,老师也曾召集全体高年级女同学,秘密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月信、该怎么保护身体,还派给免费的卫生巾。我们七手八脚的接下,藏进口袋里。
“老师跟你们讲什么了?”
回到课室里,男同学盯住我们看。女同学一个个很局促。大约从我们的脸色知道是怎么回事,顽皮的男同学大着胆子说:“我知道,老师跟你们讲‘来月经’的事!”那眼光分外有神,一副很神气的样子。“哦,原来是流血了!”另一些男同学喊叫起来。一定是有人当探子,跨上扶梯跟上去,窃听回来。
覆盖在新校舍的阴影里,有一片小沙地。沙地上有一块长条木板,快要烂尽了的。体育课,老师让我们在那里跳远。有同学诡秘地说,那是腐朽了的棺材板,被日本鬼炸离身体的女人头埋在里边!同学的话很邪,我们跳远,耳朵就听到咯拉咯啦的骨殖声,鼻腔也感受到尸体的气味,死亡的气味,持久不散。我们越跳,腿越抖,生怕一不小心,就踩上森森白骨,把它抱进怀里。
滴答,滴答。
阴湿的厕所,涓滴的流水声像一首悲歌,冷冷悠唱。曾有女同学在里面撞见厉害的女鬼,有不用脚走路能漂浮的本领。她喊叫着逃出来,招来凄酸的哭夭。为了确信自己还活着,要我们用手大力掐她的肉。此后,人有三急或上体育课要更衣服,我们总拉个伴,牵手走进同一个单间。“转过去,不许偷看哦!”曾经,我等了那么久,回转过一次头,瞥见女同学水红色的背心里蓬鼓鼓的,仿佛怀抱着两只小白兔。
教师楼后方,有一间乒乓室,与牙科室毗连。定期给我们检查牙齿的护士长身穿熨得板正的白色制服,头发剪得短短的,过分整齐的牙齿,失去真实的感觉。她模样凶。她的眼睛她的头发她的牙齿她的姿势,全是骂人的武器。牙医替我们洗牙,口腔积满了水,我一阵阵恶心,忍受不住。牙医替我们补牙,机械发出难听的嗞嗞声,钻入耳朵,我极力挣扎。护士长霍然过来,伸手镇住我的身子。她脸色恼火,一开口就暴骂:
——不要动听不懂?
——又动,又动!
那嘶哑的喊骂声,一如巫婆的符咒,令人额头出汗。她只差拿绳索捆绑我,她只差用口咬我。
岁月流逝,为我们带来无数甜蜜与辛酸,变化与怀念。不知过了多少年,校庆日,母校向我们招手。我和几个小学同学带着记忆归来。陌生的警卫亭内,保安人员在站岗。新建的“沈慕羽礼堂”,冷冷地觑着我们。同班同学一大半已失去音讯,科任老师大多退休了。我们在校园内到处走走,停留了许多时光。
我看到一个女孩身穿深蓝色校裙,手中握着一本诗集,依在走廊围墙边,瞭望向远方。一阵风吹来,她那飞扬的头发,清秀干净的侧影,如同做梦的眼神,透着说不清的熟悉。我蓦然一惊,仿佛忽然和自己的前世相遇。
老同学轻拍我的肩。“走吧,发什么呆?”她指着从前上课的课室说,“我们去里边看看。”
我们推开门板,蹭了进去。里面的桌椅,都显得那样那样的小。老同学拿起粉笔,叽叽喳喳在墨绿色黑板上写了一句:六紫班,儿童节快乐!我也用彩色粉笔画上圆的方的气球。那些停留在视觉上的气球有草莓色,有蛋黄色,忽然都醒了,伸着懒腰,翻转身体,轻盈盈向上升,向上升,向上升,宛若盛开的蒲公英,风一吹,飘远了。
砰,砰!——是门板忘了栓上,被风吹开了,来回开合的声音。
砰,砰!——是长廊上男孩刺破女孩手中气球的声音。他们你追我赶,骚动起来,活泼、年轻,真正快乐。
我们含笑望向出去。那童年的滋味啊,就那样包围着我们,很香,很甜,好像很近,又似乎很远。
第14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亚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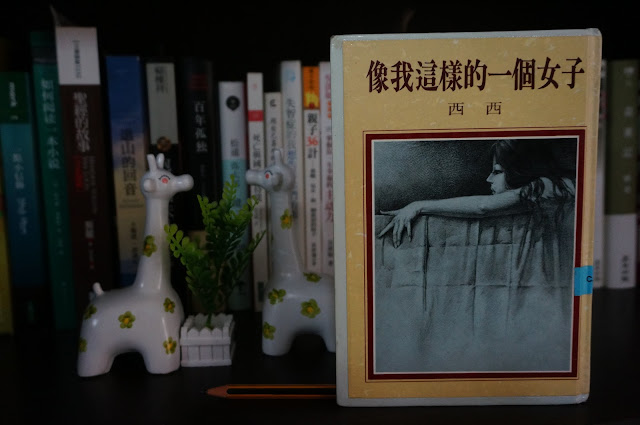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