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君子
一下到了年关,《马华文学》主编蔡晓玲邀稿,曾写下什么,已印象模糊。感谢十二月天,刊物发到家门。写吧,像瘾君子一样,戒不掉、戒不掉。
故事从一个问题开始:“制服团体的教练滥用私权,给学员带来各种困扰:向男学员索钱,向女学员毛手毛脚,违令者禁考……”心里有一把对抗的声音。我钻入稿纸的四方格里,进入一个叫做“创作”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别于现实里的他,在公在私,教练严守纪律,对学员关爱、尽责,死亡却朝她逼近;有长着翅膀载着学员飞天的卡车,笨重而轻盈……
这些为我服务的人与物,把我带进温馨、梦幻又悲恸的境地,我为人物的结局落泪,对现实的愤懑与不满,得到了救赎。那是高中第一次进行小说创作,作品寄去文学奖,误打误撞得了优秀奖。创造世界里的一景一物,获得评审的肯定,我感到踏实的安慰,也初尝创作的魔力。借由这个起点,我发现当小说被创造出来,生活中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就能够在虚虚实实的情节里,把它当成小小的百老汇演出,并学着放下。
和文字一起探索改变内心煎熬的各种可能性,令人振奋。丑恶的人,给予他新生命,他能够以和善的面目重新来过吗?心灵的苦楚、身体的疼痛,有没有办法完结?有可能到达向往的远方吗?
升上大学,课业繁忙,我和一群文艺爱好者在学长、学姐筹办的《溪林佴编辑室》社团,有的当上记者,有的成为作者,开会、采访、撰稿、编辑、出版、销售……我所属的文艺组,组长后来于北马某报刊担任主编,记忆中,往时的他,擅写情诗,刊物上常见他的诗作。而我则在《溪林佴》封底占一个版位,一图一文,言简意赅,是短诗也是小品。
每期刊物一出版,就有固定的读者向我们订购。获悉我参与编辑室活动的系友,却痛斥我“不务正业”,“搞什么文艺创作”。知与不知,何必多言?我和创作,确实曾经有一度很亲近。但是建筑系院毕业生,根本不适合拥抱这种志向。随着学年的增长,我再也无法朝两个方向迈开脚步。接下来几年,别说创作,我连中文读物都疏远了。
然而,此生爱上创作的人一定明白,一旦染上创作瘾,想戒也难。在创作的时空里,可以天马行空,沿途没有任何阻扰,思绪只要到达那里,笔下的人物便置身于那幻想的空间。
当老板挥挥手说再见哦不要留得太晚我却为第二天他要带上飞机到国外开会的设计图未修好而抓狂,当人们睡熟了我才拖着躯壳从办公室出来按铃招德士,当准时下班挨挤在汗酸味蒸腾的地铁站里一动不动,当路过商场高跟鞋踢踢踏踏人们抢购优惠价名牌衣衫掉在地下被踩成七彩衣尸……你不知道我在心里遇见了什么。
回来吧,文字从我看不到的地方跑了出来,朝我召唤。
尽管岁月早把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毁灭,我的文学底子也根本不那么好,在所有创作者面前我都觉得渺小,但是我踩不下煞车,一路奔离职场,投向文字的怀抱。我在做什么呀?
“就算所有读者都消失了,只要还剩一个,就会有人继续创作。创作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文学创作是不会完全消失的,只是趋于小众化,或转换成其他的形体,传承下去……”参与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中文系联办的学术工作坊《大时代与小片段:现代短篇小说的问题功能与艺术精神》,主讲者吴德利副教授在回应观众提问时,如是回答。我想,那就是创作者对于创作之戒不掉的瘾了。
2018年九月《马华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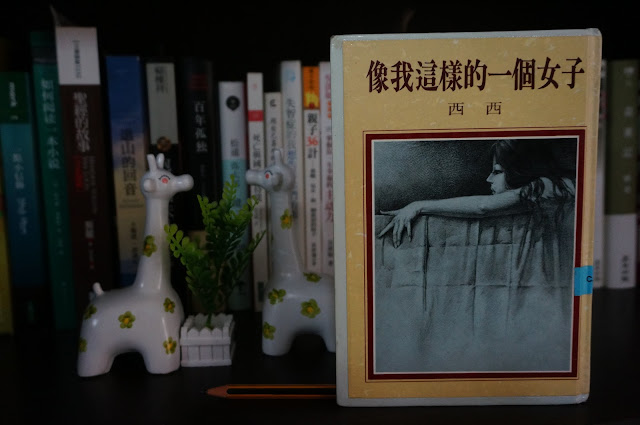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欢说得太好,写小说确实是种救赎。
回复删除为自己写,不然就为蝉、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吧[村上春树]
谢谢阿reen=)
删除为自己写,不然就为蝉、蛙、蜘蛛以及夏草和风写吧——啊啊深得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