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P-Ramlee
 |
| 图/文:叶家乌贼 |
地铁站内,一名三十左右的男子,拎着大塑料旅行袋,走了过来:“请问去文礼是这道列车吗?”我点点头说:“是的。”
地铁驶进站,门打开了,我走进地铁,男子跟进车厢。“你也去文礼啊?”他问。我微笑不答。他坐下,拍拍隔壁坐位说:“来,来,我们一起坐,聊聊天。”我没搭理,就着门边站。“我妹妹住文礼,我们许久没见面了……”他继续说:“我差点以为你是我妹妹呢!”我白眼一翻,往车厢尽头远远走去,背贴着车厢站立。
“这么多位子不坐。”男子大声地自言自语。“喂,新加坡人!”他忽然指着我喊叫起来:“我问你,为什么你们那么爱站着?是你们的政府教育你们不许坐下吗?”车厢上稀疏坐着几个人,全望了过来。
我吃了一惊。男子是不是精神出了状况?要是他突然发狂攻击人,该怎么办?——将近半夜的晚间十一点钟,在治安良好的新加坡,需要搭夜班地铁时遇上这样的情况,难免也会令人感到不安。
当然,也许他是一个乡下人,从遥远的地方来探望妹妹,对城市人的淡漠浑然不知,才会冒然、唐突地说了一席怪话。然而,过往经历让我不能不抱着提防之心。
中学时期,每日放学我走路回家,途经高尚住区、茅草原野、马来甘榜,一路上,看看蓝天,有白云悠悠飘向天边,太美太美;也遇过让人窒息地往回家路上跑、各种疯子和变态狂的黑暗:有人形貌猥琐,躲在草丛中,路过时忽然跳出来,拔出一只毛茸茸的小鸟,张着翅膀兀自乱震,眼球凸起,享受地嗤笑;有人衣衫整齐,骑着脚车越过行人,冷不防泼出一罐奶白色液体,腥臭逼人,浆糊似刷硬一头长发,淫邪透顶;也有人披头散发,冲向路人,举着木棍往路人肩膀上猛力敲击,狂笑跑开……
这不是小说,情节虚构,而是使劲摇头,也摇不去的可怕往事、魔鬼的笑靥。
离开古城,到雪隆生活时,也一样活在不安与恐惧中。暮色中,公寓楼下那些紧紧缠住、跟踪下班女子的黑人大只佬,不只满口花言巧语,在下班后加快了回家的脚步,也于噩梦中,一次次化身为隐匿在幽暗长廊,露出发亮眼睛和牙齿的兽,把自己惊醒,一身湿汗,两手冰冷。
搭KTM火车,一样遇过奇怪的事。有一次,一名男搭客闯进了女性车厢。他一下说自己是国王,一下自称歌王P.Ramlee。他手里握住一根盲人杖,不断骂说:“我不臭!我哪里臭了?”且使尽力气,朝地下一个褪色的行李箱,狠狠地踢,想要把它如坦克驶过给碾个扁平似的。
“我有去毛,我有洗澡!”他说:“你们以为只有你们的腋下才香吗?我的腋下也很香!”言语猥琐。还把手抬起来,头压下去、压下去,闻嗅他腋下。戏剧化一幕,毕生难忘。
每每遇上这些事,难免把我复杂的思绪搅得更复杂。他们究竟遇上何事,致使精神失常?暴露狂心理变态,原因何在?身份变幻之快如川剧变脸的盲人,说别人瞧不起他,是双目失明,饱受歧视所致?
所有疑团,无人解答。社会压力大,人们步履太匆忙,自身难保的年代,谁有闲暇去关怀这些需要治疗的群体,阻止他们进一步骚扰平民百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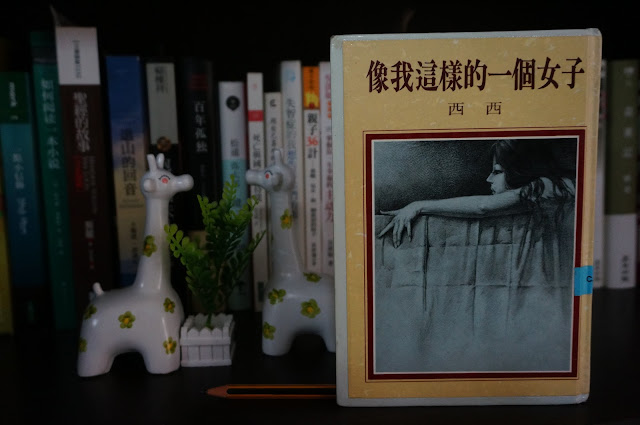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