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妹仔孖的一样!
佳节期间,住在吉隆坡的叔叔常带着家人远道探访我们。
父亲跟叔叔感情要好。每每相聚,受英文教育的他以客话跟父亲闲聊;对我们则以英语夹杂不大标准的华语,浅谈几句。跟严肃的伯伯不一样,叔叔年轻又摩登。他的脸上,时时挂着笑容,——那眉眼,不笑时也像笑着。叔叔老穿牛仔裤搭简便衬衫。他的头发,梳得油亮油亮。退休以前,叔叔是一名摄影师,经营一家照相馆。嗜好摄影的我,对他自然很有些景仰。儿时我们举家到吉隆坡游玩,就由叔叔替我们照相留念呢。
婶婶更讨喜了。她说话七情上面、比手画脚。但她不似许多欧巴桑,满言满语都是亲朋戚友的闲话,说时脸微微一侧,一只手掩在嘴巴上,把别人说得要多坏,有多坏,提起自己,则自夸不已。不管对谁,婶婶多是赞美之言。她言语诚恳,并非奉承阿諛,更多是心地善良;在她眼中,几乎一切都是美好的。若听见旁人说起某某的闲话,顶多也只是“哦哦,这样啊”地敷衍几句,不加油添醋。
婶婶逢人就赞美。她尤其赞赏我哥:“啧啧啧,安靓仔!我女儿讲你很像陈豪,安靓仔……”陈豪是当年的师奶杀手,她这么说,我哥立马摇头道:“哪里像啦!”随即赞起婶婶:“嗯梅(五婶)你才是越来越瘦,很年轻!”每当这时候,她就跳起来,猛挥手叫道:“唉哟,你看我,肥到要死!肥嘚嘚!”边说,边用手挤出肚腩,捏一捏,拍一拍,振一振,脂肪跳跳、跳跳,笑得我们合不拢嘴。
有一次,她赞我越来越漂亮。看到妹妹,她也赞:“越来越漂亮了!”接着又说:“你们两个都长大了,长高了,长漂亮了!”父亲回答:“你的孩子也一样呀,全长高长漂亮了,我们都几岁了……”婶婶指着我和妹,告诉父亲:“你的孖的一样。”“什么?”父亲嘴巴张着。婶婶重复:“孖(妈)的!孖(妈)的!你的孖(妈)的一样!”
她那表情,过分认真。经常追看港剧、熟悉粤语的我和妹妹,一下笑颠了身子。“她讲我们很像双胞胎啦!”我和妹妹向父亲解释,同时告诉婶婶:“我爸以为你骂粗话!”她一双手又急急挥作一团了:“哎哟,不是,不是!”
婶婶养过一只鹿狗,瘦瘦瘦瘦的,体型娇小,走起路来却很灵巧,一双蹄儿“笃笃、笃笃”,响个不停,像梅花鹿越过原野,煞是动听。叔叔和婶婶带着鹿狗到访,离开前,母亲顽心一起,抱着鹿狗不放,叫婶婶假装要离去。叔叔一家走向门外,鹿狗挣扎、尖叫,急了,眼泪啪嗒啪嗒流下。婶婶冲进来,把它紧揽怀中,眼睛也湿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只狗会哭泣。后来它意外丧命,每一次婶婶提起,眼泪都止不住。
岁月无情,生命无常。痛失爱犬的叔叔和婶婶,多年后又遭遇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撕心裂肺。他俩消瘦下去,头发白了,脸憔悴了。
时光慢慢慢慢。堂姐往生,好些年了吧!听父亲提起,叔叔将进行一项手术。多几天妹从国外回来,早已约好携带双亲去探访他。远在狮城的我,惟有默默祷告:愿叔叔平安无恙,合家安康。
链接:叶家乌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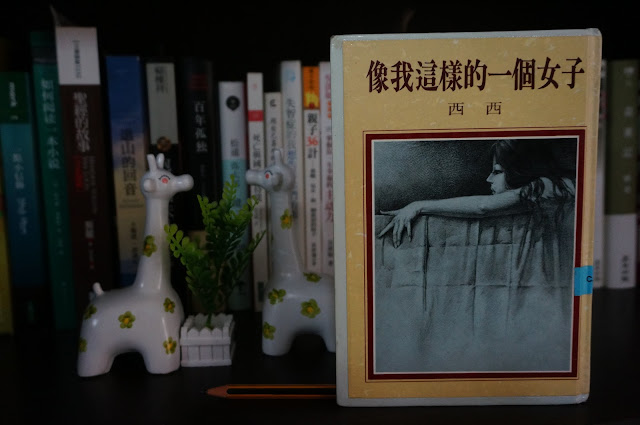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