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鱼的老人、南洋大学与云南园
11月13录用的这篇稿,刊登的时候,爸爸你却往生了。爸爸我写我们一起走过的足迹、你跟我讲过的点点滴滴,你知道吗?文章里我常提起你,你懂吗?爸爸,我的生活怎么能缺了你?然而我并不愿爸爸你留恋这里,我希望现在的你在天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如果你偶然读见了人间的这篇稿,你隐隐然觉得熟悉,嘴角扬起了莫名的微笑,我就心满意足。——永远爱你的女儿。
 |
| 想你…… |
“刚才喂过了!”他说。骑着脚踏车、穿着白运动鞋,他手拿一袋面包,走向我们。正在湖心桥上看伴侣喂鱼的我,本来沉浸于二人世界中,没兴致搭理他。伴侣喜欢喂鱼。每次回老家,我都跟母亲要旧面包给他。如今疫情困我俩于这座城,经久没回老家,所幸居住在校园内,南大湖与云南园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在今年初重新开放后,水体面积大幅度增加,四周栽植了不少树木,到处都是花,有的白,有的紫,有的嫣红,高高低低的植物,吸引来百鸟齐鸣,蝴蝶、蜜蜂、蜻蜓和豆娘,全来凑热闹,湖里的鱼儿,也缤纷多姿。每逢周末,我和伴侣追蝶赏花探豆娘,时而逗弄湖里的鱼儿愉快地张嘴吃,也算一解乡愁。
“这有斑的是老虎鱼。”他又抛出一句话。我瞄他一眼。他看起来六十有几,皮肤阳光色,双眼有神,肢体矫健。他口里说喂过这里的鱼,手中却抽出一大片面包,撕开来抛向水中。噼里啪啦,鲤鱼红白相映,争先恐后抢食去。它们嘴巴一张,面包一口咬下。刚才我和伴侣投向湖里的玉米谷片屑,它们可意兴阑珊哩!唯有小鱼兴致勃勃地抢食。也许分量太小吧!这些鲤鱼,委实好命!我白眼一翻。老先生的出现和“抢生意”,使聚集在我和伴侣面前的大鱼,一股脑儿涌向他那里去了。
“你每天都来喂鱼?”我随口问问,然后抿着唇,盯着抢食的鲤鱼。“差不多天天来。”他答。随即摇一摇手中面包道:“才块二钱,一大包。不然没的吃啊,很多鱼。”“有时,我会买两包……”他又说。我心想:“怎会没得吃?很多人喂呢,这里的鱼!”常流连云南园的我可清楚了。要喂鱼,得赶早。若鱼群被喂饱,便不稀罕喂食:它们早就吃撑了肚皮,再吃,翻鱼肚白啦!但是见这名老先生如此关心鱼们肚子饿不饿,是好人无疑,到底对他产生了好感。
“1983年,我在这附近养鱼。”他一句话,使我精神抖擞。“养在哪里?”我边问,边抬眼看看云南园前方,那高耸入云的租屋群,揣想时光退回到三十几年前,会是怎么一个光景?肯定不是现今的模样,也不会是养在层层往上建、新加坡近年设立的垂直养鱼场;但从前的样子,一时想像不来。“池塘。”他追溯:“我们挖池塘养鱼。以前这里很多养鱼的,我们把鱼卖到各地去……”与伴侣对望一眼,我耸一耸眉毛。
“我以前有养老虎鱼。”老先生说。“我也是买面包给它们吃,去面包店买。鱼苗我们买四分,卖五分。后来政府赶我们……”他娓娓道来,语气不悲也不喜,难掩的是怀念之情。他的现况,应该挺不错。至少相对那些驼着背在小贩中心收碗碟、在公厕当清洁工的白头老叟和老妇,他有闲暇骑脚车游园、有闲钱买面包享喂鱼乐,勿须着急自己的胃。当他提及四分和五分钱的时候,我的脑海涌现了父亲跟伴侣聊天时,谈起他从前吃一碗面、卖一个鸟笼的价钱,一样是以几分几分来计算。一阵晨风吻上我的脸,柔柔的,我眯眼微笑,十分惬意。
我扶着护栏,往水中看。老先生口中的老虎鱼,比鲤鱼小,比kapis鱼(guppy鱼?)大,身上有美丽的黑纹,鱼肚微微地泛红。它们穿梭于鲤鱼和kapis鱼之间,构成一幅生动的画。原来老先生养过虎鱼,怪不得他对虎鱼情有独钟。“老虎鱼会长到多大?”伴侣好奇地问。老先生伸展拇指和食指至十厘米左右的宽度表示:“大概这样,不会多大。”
他又撕一片面包,丢向水中。鲤鱼一口口吞下。涟漪一朵朵散开,彼此交叠着。“以前这里是南洋大学啊,华文的。”老人抬眼看我们,忽然这么说。我和伴侣点点头。我们知道呀!然而我们静而不答。
第一次带父亲来南大,他再三交代,想去云南园和南大湖看看。在父亲十几岁少年时,1958年吧,他曾和当时的雇主千里迢迢赶来新加坡,出席南洋大学的落成典礼。一所华社筹款建成的大学,对当年的华人社会,意义非凡!政商精英、贩夫庶民,全到场观礼。作为当天盛况的见证者,父亲每每追忆起,犹双眼发光,热血澎湃:“密密麻麻、万头攒动啊,排山倒海的人潮……”
以前,以前啊,曾经养鱼的老人仿佛清描淡写,内心藏着的,或是诉不尽的千滋百味。撒一把盐、浇一滴醋,时光具有魔力,回首,怎不教人惆怅?
大概想起我们之间曾多次谈论,关于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变革、云南园和南大湖的翻新等各种看法,伴侣问老人:“喜欢以前还是现在的云南园和南大湖?”并低声告诉我:“应该是现在吧,他喜欢喂鱼。”老人却答非所问:“以前湖很浅……”然后指向南大湖的另一侧,那Canteen1的方向告诉我们:“我十多岁时,在这里的食堂做工……”
他也许有更多的故事,想告诉我们。我追问下去,说不定可以重返一趟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南洋大学,亲历那与今日或全然迥异的境地。然而,另一个老人,一路拍着手,“啪——啪——”来到我们跟前。他大概在晨运,也许平日常相遇,他与曾经养鱼的老人用福建话交谈起来。哦不,是潮州话吧!我是半个福建人,细听我不大明白的,多半是潮州话。
曾经养鱼的老人边把面包收起,边告诉拍手的老人和我们:“要留一点,去另一边喂鱼。”我们挥挥手说Bye bye!他骑着脚踏车去远,我和伴侣也往反方向走。只留下拍手的老人一声声:“啪——啪——”
“没养鱼了,还是喜欢鱼。”踏离云南园之时,伴侣喃喃。园丁用割草机碾过的草坪,散发出草的芬芳,似远,犹近。
《星洲日报·星云版》2020-1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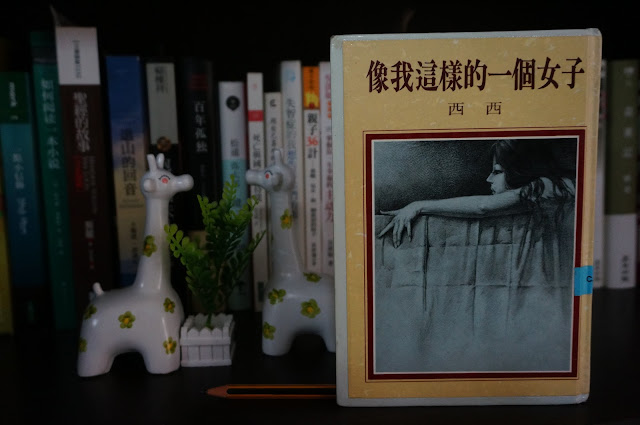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