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的是胃,还是心?
梦太美。我和父亲一起聊天,吃着面粉粿,太好吃。面粉糕的好搭档——是自家种的money菜(Manis菜)煮的汤头,格外鲜美。端起碗,我把碗底也舔个发亮。吃完才想起,父亲掉了半数牙,那一片片带点厚度的面粉粿,会不会很难嚼?我问,他笑而不答。我知道,父亲煮些什么,不都以我们的喜好为主。
无数只猫,咪嗷、咪嗷叫,冷冷的猫爪来碰我的脚。我缩起脚,感觉恶心。它们脏,它们臭,一身湿嗒嗒的毛,是混夜市惹来的狼狈。睁着蓝的、绿的冷眼,猫们要抢食。哥拉着我的手,一路找到卖Putu Piring(马来式嘟嘟糕)的摊子,太高兴,我们买了Putu Piring,边走边吃。雪白雪白的蒸糕折半,漏出吸饱椰糖浆的椰丝,一口接一口,吃完还想再吃。夜市位于新山,是大学城吗?又似雪隆回马六甲途中的某一个小镇,——那多少次,出现梦中的情景,熟悉又陌生,我一度怀疑,它们是真实的另一个空间。阿蓉(我妹),也买了一份美味小食,我心动了,但夜市人太多,太拥挤,难以穿过人群寻回那一个小食摊,咦——夜市的地点,仿佛又是马六甲的住区Taman Pringgit Jaya,眼熟却又不全然一致,同样在梦中多次出现的场景……
我被猫爪触及,醒了。只是梦啊,真的吗?肚子咕噜咕噜乱叫,胃涨得有点疼。也许最近胃口不好,吃太少。
不放过我的猫们,是当年工大宿舍里流连垃圾桶、整条走廊乱窜的肮脏猫,猫魂不散?面粉粿……不久前听父亲说的,听从我的提议买了一包面粉,还没用。“做包啊!”我说。花生包是母亲的拿手包点,从最初的“石头包”演变成后来的“好吃包”:花生要现炒现磨,包要等面团发酵足了,才裹入馅料。垫包的香蕉叶,到菜园现摘,洗净擦干备用……花生包是父亲的最爱不是吗?他却说:“你们回才做的。”母亲已忘了怎么做包,我们不在身边,父亲也提不起兴致做包吧。“那煮面粉糕咯!”我又说。佐以江鱼仔、指天椒的面粉粿,光想起就谗涎欲滴。“不会饱。”父亲摇摇头,这才告诉我,炒米粉和面粉粿都无法让他果腹,不管吃多少,很快就感到饿。“只有吃粥才会饱!”他说。多年过去,父亲依然与他儿时家中非常贫困的年代一样,习惯以粥水连同粥,才足以果腹。也是第一次,得知以前我们家每个周六的家常菜面粉粿和炒米粉,都是父亲所不爱的食物。我一直以为自己挺了解父亲,原来连生活中,他对家人最朴素的贴心,我也并不知晓。
不再能和父亲聊天说话以后,白天我尽力不多想,努力像平时一样过日子。梦里却一次次遇见父亲,那么真实、那么亲密地坐在我身侧。清醒时分,拭干泪湿的眼。看看时钟,是上午七点半。每次回老家的此时此刻,父亲早已在厨房忙了将近一个钟,蒸出了热腾腾的金瓜糕、芋头糕,或者炸了芋头夹年糕、开了椰子取出水和肉,等等,等等。现在,它已成了过去式。Putu Piring呢,有十几年没吃了吧?在雪隆念硕士班的日子,每逢周末都会跟着哥哥、妹妹一同去三姐家、都会在她住区花园前买Putu Piring,给三个小瓜和大家一起吃。有时父亲、母亲也在那里。那时候三姐念博士班,同时看顾三个小孩。每当她忙不过来时,摇一通电话,视力还没被青光眼吞噬的父亲,就会开车载着智力尚未被失智症啃咬的母亲,千里迢迢到三姐家帮忙,也能多见见在外地生活的孩子们。小瓜们跳着,三姐叫着,叽里呱啦,嘻嘻哈哈……
啊,好想吃Putu Piring。
连结:叶家乌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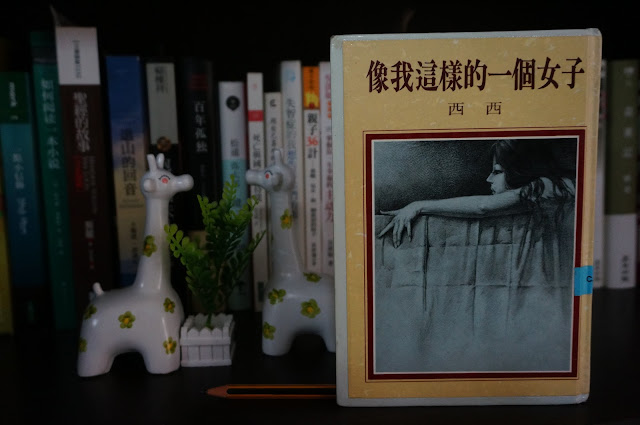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梦里都是吃的,看来你真饿了,哈。我父亲很爱吃刀麻切,家里的搅面机都是他从星加坡扛回来。小新要买putu piring应该不容易吧?这类小吃在城市还真少见。
回复删除节目中见过,不过离我住区远,小新说小,从一处到另一处还是很花时间。
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