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薯收成记
种了一年的木薯绿成荫,顶端小花成簇。斩下其中一棵,收割的木薯比手臂胖,比前臂长!幸好纤维未老,煮至熟软,撒上白糖,筷子轻松一插就穿,松嫩美味。
小时候,每当父亲要“杀木薯”,我总是蹲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刀起刀落,把木薯斩成几段,然后刀子沿着木薯边缘,轻轻划出一条细长的线。他将刀尖嵌入木薯与外皮之间,小心撬开。随着一圈圈的剥离,白皙的木薯露了出来,外皮如同干枯树皮般脱落。最后,父亲将剥好的木薯放入盛满水的锅中煮熟(即杀木薯),美味朴素的早餐,让人满心欢喜。
有时,父亲会把木薯刨成丝,加入椰丝和黑糖,蒸煮成糕。在我们家,这种木薯糕被称作“眨眼糕”。据说,哥哥小时候看父亲做木薯糕,边眨眼睛边问:“爸,这是什么糕?”父亲打趣道:“眨眼糕!”那一眨眼,几十年匆匆流逝……
蒸好的木薯热气袅袅升起,刚吃过早餐的我明明很饱,闻见那朴素的香气却还是忍不住盛了一碟,撒上白糖,享用起来。
木薯好好吃!可依稀记得父亲或母亲曾说过,木薯不宜多吃!日据时期,食粮缺乏,只有野生木薯长得茂盛,人们收割其根茎,果腹充饥,结果和野生蕹菜吃多导致“脚软”一样,单吃木薯亦营养不良。
前阵子,参加《城市生活的自然写作》工作坊时,刘老师提起,他品尝了朋友送的酒酿木薯,味道极佳。一听到这甜食,便想起姐姐酿的鲜甜米酒,与我爱吃的木薯仿佛一霎时在舌尖共舞,软绵香甜,滋味美好。“好吃!”我吞咽下口水赞道。“你吃过啊?”刘老师问,我一时无言以对。有机会,真想尝试。
刘老师把木薯称作树薯,我这才知道木薯也叫树薯。刘老师还说,木薯叶也可食用。妹妹告诉我,她吃印尼餐时尝过一口,味道并不讨喜。我对木薯叶的滋味不感兴趣,却在一次阅读中得知,木薯含有氰甙,在未经过适当处理时,可能释放出具毒性的氰化物。因此,木薯需要充分浸泡并长时间烹煮,才能有效地降低木薯中的毒性,确保安全食用。难怪父亲煮木薯时,水总是淹没木薯煮至松软,而非隔碗蒸熟。
工作坊结束前,同学们办了一场美食会。其中一名对植物颇有研究的同学端出了亲手做的木薯糕。那木薯糕裹满椰丝,外观与传统木薯糕不很相似,但咬上一口,我立刻爱上它,软糯香甜,十分开胃。刘老师也忍不住尝了三块!请教同学配方,她告诉我非常简单:一公斤木薯、一粒椰浆,加香兰汁和黄糖,蒸好后裹上椰丝。同学又说,那是菜市场摊主亲授的食谱。她一试,果然让我们都为之惊艳!
同学的椰香木薯糕美味,姐姐的西米木薯糕也别有一番风味。吃完新鲜收割、热腾出炉的水煮木薯,姐姐的木薯糕也上了桌。那混合着黑糖与木薯的香气,令人难以抗拒。这下子,五脏庙祭得也太丰盛了。
那每一口的木薯与木薯糕,都承载着童年的记忆:父爱的温暖以及朴实生活的美好。时光流转,木薯始终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永不分割。
专栏:叶家乌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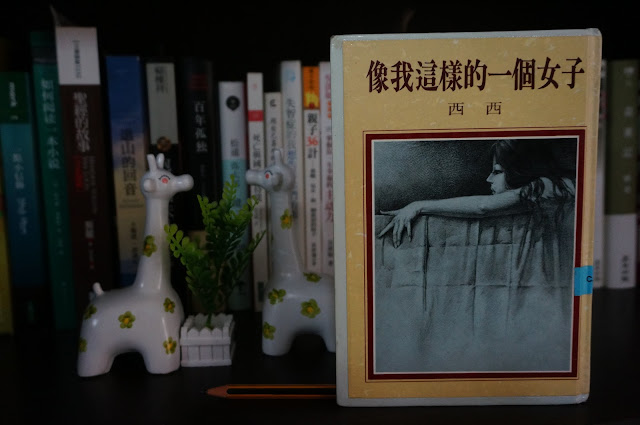


小时娘家前后都有种植木薯,不一样的品种,我婆婆是种来喂鸡。我妈妈有时会种几棵可以做木薯糕的木薯树, 一蒸就是一大盘,很可怕的份量。对我来说最好吃的木薯糕是刚蒸好乃带温温和带软的时刻,隔夜后我就不感兴趣。木薯叶煮椰汁我是在公司食堂看过, 第一次看见才知道木薯叶子原来是可以煮来吃的!!!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所以不知道味道如何。 ~SK
回复删除我们家基本上留不到过夜,好好吃很快会被扫光!
删除咦怎么不能接受,哈哈,sk姐好可爱!番薯叶呢番薯叶?难道和我妹一样敬而远之?
木薯叶子纤维很粗,怕是也没什么味道,要不然当年我婆婆应该也会拿来喂鸡,通常我们是砍下木薯叶子丢掉哦。
删除蕃薯叶我很喜欢吃,嫩嫩的蕃薯叶都带甜味,清炒最好吃。
哈哈,原来如此,我家木薯叶也是丢掉的,不过知道可食用后会有点好奇。
删除番薯叶小时候我超怕的,现在却超喜欢=)